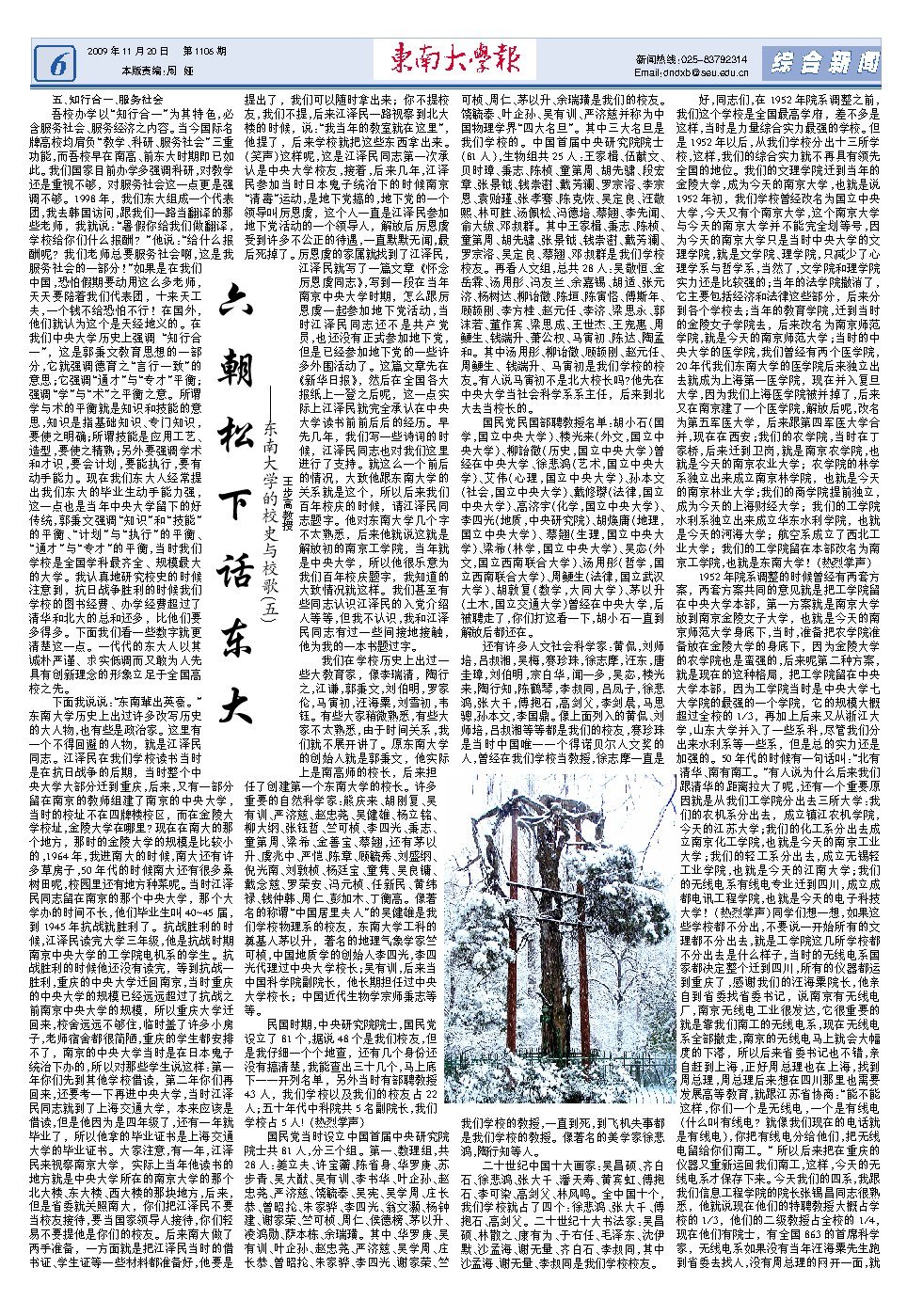五、知行合一、服务社会吾校办学以“知行合一”为其特色,必含服务社会、服务经济之内容。当今国际名牌高校均肩负“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三重功能,而吾校早在南高、前东大时期即已如此。我们国家目前办学多强调科研,对教学还是重视不够,对服务社会这一点更是强调不够。1998年,我们东大组成一个代表团,我去韩国访问,跟我们一路当翻译的那些老师,我就说:“暑假你给我们做翻译,学校给你们什么报酬?”他说:“给什么报酬呢?我们老师总要服务社会啊,这是我服务社会的一部分!”如果是在我们中国,恐怕假期要动用这么多老师,天天要陪着我们代表团,十来天工夫,一个钱不给恐怕不行!在国外,他们就认为这个是天经地义的。在我们中央大学历史上强调“知行合一”,这是郭秉文教育思想的一部分,它就强调德育之“言行一致”的意思;它强调“通才”与“专才”平衡;强调“学”与“术”之平衡之意。所谓学与术的平衡就是知识和技能的意思,知识是指基础知识、专门知识,要使之明确;所谓技能是应用工艺、造型,要使之精熟;另外要强调学术和才识,要会计划,要能执行,要有动手能力。现在我们东大人经常提出我们东大的毕业生动手能力强,这一点也是当年中央大学留下的好传统,郭秉文强调“知识”和“技能”
的平衡、“计划”与“执行”的平衡、“通才”与“专才”的平衡,当时我们学校是全国学科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大学。我认真地研究校史的时候注意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图书经费、办学经费超过了清华和北大的总和还多,比他们要多得多。下面我们看一些数字就更清楚这一点。一代代的东大人以其诚朴严谨、求实低调而又敢为人先具有创新理念的形象立足于全国高校之先。
下面我说说:“东南辈出英豪。”
东南大学历史上出过许多改写历史的大人物,也有些是政治家。这里有一个不得回避的人物,就是江泽民同志。江泽民在我们学校读书当时是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当时整个中央大学大部分迁到重庆,后来,又有一部分留在南京的教师组建了南京的中央大学,当时的校址不在四牌楼校区,而在金陵大学校址,金陵大学在哪里?现在在南大的那个地方,那时的金陵大学的规模是比较小的,1964年,我进南大的时候,南大还有许多草房子,50年代的时候南大还有很多桑树田呢,校园里还有地方种菜呢。当时江泽民同志留在南京的那个中央大学,那个大学办的时间不长,他们毕业生叫40~45届,到1945年抗战就胜利了。抗战胜利的时候,江泽民读完大学三年级,他是抗战时期南京中央大学的工学院电机系的学生。抗战胜利的时候他还没有读完,等到抗战一胜利,重庆的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当时重庆的中央大学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抗战之前南京中央大学的规模,所以重庆大学迁回来,校舍远远不够住,临时盖了许多小房子,老师宿舍都很简陋,重庆的学生都安排不了,南京的中央大学当时是在日本鬼子统治下办的,所以对那些学生说这样:第一年你们先到其他学校借读,第二年你们再回来,还要考一下再进中央大学,当时江泽民同志就到了上海交通大学,本来应该是借读,但是他因为是四年级了,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所以他拿的毕业证书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证书。大家注意,有一年,江泽民来视察南京大学,实际上当年他读书的地方就是中央大学所在的南京大学的那个北大楼、东大楼、西大楼的那块地方,后来,但是省委就关照南大,你们把江泽民不要当校友接待,要当国家领导人接待,你们轻易不要提他是你们的校友。后来南大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就是把江泽民当时的借书证、学生证等一些材料都准备好,他要是提出了,我们可以随时拿出来;你不提校友,我们不提,后来江泽民一路视察到北大楼的时候,说:“我当年的教室就在这里”,他提了,后来学校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笑声)这样呢,这是江泽民同志第一次承认是中央大学校友,接着,后来几年,江泽民参加当时日本鬼子统治下的时候南京“清毒”运动,是地下党搞的,地下党的一个领导叫厉恩虞,这个人一直是江泽民参加地下党活动的一个领导人,解放后厉恩虞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一直默默无闻,最后死掉了。厉恩虞的家属就找到了江泽民,江泽民就写了一篇文章《怀念厉恩虞同志》,写到一段在当年南京中央大学时期,怎么跟厉恩虞一起参加地下党活动,当时江泽民同志还不是共产党员,也还没有正式参加地下党,但是已经参加地下党的一些许多外围活动了。这篇文章先在《新华日报》,然后在全国各大报纸上一登之后呢,这一点实际上江泽民就完全承认在中央大学读书前前后后的经历。早先几年,我们写一些诗词的时候,江泽民同志也对我们这里进行了支持。就这么一个前后的情况,大致他跟东南大学的关系就是这个,所以后来我们百年校庆的时候,请江泽民同志题字。他对东南大学几个字不太熟悉,后来他就说这就是解放初的南京工学院,当年就是中央大学,所以他很乐意为我们百年校庆题字,我知道的大致情况就这样。我们甚至有些同志认识江泽民的入党介绍人等等,但我不认识,我和江泽民同志有过一些间接地接触,他为我的一本书题过字。
我们在学校历史上出过一些大教育家,像李瑞清,陶行之,江谦,郭秉文,刘伯明,罗家伦,马寅初,汪海粟,刘)初,韦钰。有些大家稍微熟悉,有些大家不太熟悉,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展开讲了。原东南大学的创始人就是郭秉文,他实际上是南高师的校长,后来担任了创建第一个东南大学的校长。许多重要的自然科学家:熊庆来、胡刚复、吴有训、严济慈、赵忠尧、吴健雄、杨立铭、柳大纲、张钰哲、竺可桢、李四光、秉志、童第周、梁希、金善宝、蔡翘,还有茅以升、虞兆中、严恺、陈章、顾毓秀、刘盛纲、倪光南、刘敦桢、杨廷宝、童隽、吴良镛、戴念慈、罗荣安、冯元桢、任新民、黄纬禄、钱仲韩、周仁、彭加木、丁衡高。像著名的称谓“中国居里夫人”的吴健雄是我们学校物理系的校友,东南大学工科的奠基人茅以升,著名的地理气象学家竺可桢,中国地质学的创始人李四光,李四光代理过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后来当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长期担任过中央大学校长;中国近代生物学宗师秉志等等。
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院士,国民党设立了81个,据说48个是我们校友,但是我仔细一个个地查,还有几个身份还没有搞清楚,我能查出三十几个,马上底下一一开列名单,另外当时有部聘教授43人,我们学校以及我们的校友占22人;五十年代中科院共5名副院长,我们学校占5人!(热烈掌声)国民党当时设立中国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共81人,分三个组。第一、数理组,共28人:姜立夫、许宝蘅、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杨钟建、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余瑞璜。其中、华罗庚、吴有训、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谢家荣、竺可桢、周仁、茅以升、余瑞璜是我们的校友。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并称为中国物理学界“四大名旦”。其中三大名旦是我们学校的。中国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81人),生物组共25人:王家楫、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骕、段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其中王家楫、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骕、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吴定良、蔡翘、邓叔群是我们学校校友。再看人文组,总共28人: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其中汤用彤、柳诒徵、顾颉刚、赵元任、周鲠生、钱端升、马寅初是我们学校的校友。有人说马寅初不是北大校长吗?他先在中央大学当社会科学系系主任,后来到北大去当校长的。
国民党民国部聘教授名单:胡小石(国学,国立中央大学)、楼光来(外文,国立中央大学)、柳詒徵(历史,国立中央大学)曾经在中央大学、徐悲鸿(艺术,国立中央大学)、艾伟(心理,国立中央大学)、孙本文(社会,国立中央大学)、戴修瓒(法律,国立中央大学)、高济宇(化学,国立中央大学)、李四光(地质,中央研究院)、胡焕庸(地理,国立中央大学)、蔡翘(生理,国立中央大学)、梁希(林学,国立中央大学)、吴宓(外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汤用彤(哲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周鲠生(法律,国立武汉大学)、胡敦复(数学,大同大学)、茅以升(土木,国立交通大学)曾经在中央大学,后被聘走了,你们打这看一下,胡小石一直到解放后都还在。
还有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家:黄侃,刘师培,吕叔湘,吴梅,赛珍珠,徐志摩,汪东,唐圭璋,刘伯明,宗白华,闻一多,吴宓,楼光来,陶行知,陈鹤琴,李叔同,吕凤子,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高剑父,李剑晨,马思骢,孙本文,李国鼎。像上面列入的黄侃、刘师培,吕叔湘等等都是我们的校友,赛珍珠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得诺贝尔人文奖的人,曾经在我们学校当教授,徐志摩一直是我们学校的教授,一直到死,到飞机失事都是我们学校的教授。像著名的美学家徐悲鸿,陶行知等人。
二十世纪中国十大画家: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潘天寿、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高剑父、林风鸣。全中国十个,我们学校就占了四个: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高剑父。二十世纪十大书法家:吴昌硕、林散之、康有为、于右任、毛泽东、沈伊默、沙孟海、谢无量、齐白石、李叔同,其中沙孟海、谢无量、李叔同是我们学校校友。
好,同志们,在1952年院系调整之前,我们这个学校是全国最高学府,差不多是这样,当时是力量综合实力最强的学校。但是1952年以后,从我们学校分出十三所学校,这样,我们的综合实力就不再具有领先全国的地位。我们的文理学院迁到当年的金陵大学,成为今天的南京大学,也就是说1952年初,我们学校曾经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今天又有个南京大学,这个南京大学与今天的南京大学并不能完全划等号,因为今天的南京大学只是当时中央大学的文理学院,就是文学院、理学院,只减少了心理学系与哲学系,当然了,文学院和理学院实力还是比较强的;当年的法学院撤消了,它主要包括经济和法律这些部分,后来分到各个学校去;当年的教育学院,迁到当时的金陵女子学院去,后来改名为南京师范学院,就是今天的南京师范大学;当时的中央大学的医学院,我们曾经有两个医学院,20年代我们东南大学的医学院后来独立出去就成为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在并入复旦大学,因为我们上海医学院被并掉了,后来又在南京建了一个医学院,解放后呢,改名为第五军医大学,后来跟第四军医大学合并,现在在西安;我们的农学院,当时在丁家桥,后来迁到卫岗,就是南京农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的林学系独立出来成立南京林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林业大学;我们的商学院提前独立,成为今天的上海财经大学;我们的工学院水利系独立出来成立华东水利学院,也就是今天的河海大学;航空系成立了西北工业大学;我们的工学院留在本部改名为南京工学院,也就是东南大学!(热烈掌声)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曾经有两套方案,两套方案共同的意见就是把工学院留在中央大学本部,第一方案就是南京大学放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师范大学身底下,当时,准备把农学院准备放在金陵大学的身底下,因为金陵大学的农学院也是蛮强的,后来呢第二种方案,就是现在的这种格局,把工学院留在中央大学本部,因为工学院当时是中央大学七大学院的最强的一个学院,它的规模大概超过全校的1/3,再加上后来又从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并入了一些系科,尽管我们分出来水利系等一些系,但是总的实力还是加强的。50年代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北有清华、南有南工。”有人说为什么后来我们跟清华的距离拉大了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我们工学院分出去三所大学:我们的农机系分出去,成立镇江农机学院,今天的江苏大学;我们的化工系分出去成立南京化工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工业大学;我们的轻工系分出去,成立无锡轻工业学院,也就是今天的江南大学;我们的无线电系有线电专业迁到四川,成立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也就是今天的电子科技大学!(热烈掌声)同学们想一想,如果这些学校都不分出,不要说一开始所有的文理都不分出去,就是工学院这几所学校都不分出去是什么样子,当时的无线电系国家都决定整个迁到四川,所有的仪器都运到重庆了,感谢我们的汪海粟院长,他亲自到省委找省委书记,说南京有无线电厂,南京无线电工业很发达,它很重要的就是靠我们南工的无线电系,现在无线电系全部撤走,南京的无线电马上就会大幅度的下落,所以后来省委书记也不错,亲自赶到上海,正好周总理也在上海,找到周总理,周总理后来想在四川那里也需要发展高等教育,就跟江苏省协商:“能不能这样,你们一个是无线电,一个是有线电(什么叫有线电?就像我们现在的电话就是有线电),你把有线电分给他们,把无线电留给你们南工。”所以后来把在重庆的仪器又重新运回我们南工,这样,今天的无线电系才保存下来。今天我们的四系,我跟我们信息工程学院的院长张锡昌同志很熟悉,他就说现在他们的特聘教授大概占学校的1/3,他们的二级教授占全校的1/4,现在他们有院士,有全国863的首席科学家,无线电系如果没有当年汪海粟先生跑到省委去找人,没有周总理的网开一面,就没有你们信息工程学院!(热烈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