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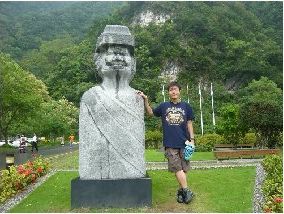
传说,一五四三年,一群葡萄牙水手在漫漫无边的太平洋中第一次发现这个风光无边的岛,情不自禁地呼出“Formosa!”,意即“美丽的岛”。四个半世纪之后,坐在隔海相望的大陆的家中,我在相片和文字里试图重新发现台湾这座美丽岛。
《胡步台湾》几度提笔,又几度搁笔,每年都有学长学姐去台湾的各个大学交换学习,每年也都有学长学姐在校报上撰文回忆,我还有必要写么?如果这只是一篇单纯的游记,或许随兴所至早已洋洋洒洒地写下大把回忆和感动。然而我总试图强迫自己撩开感性笼罩的面纱,用产业、城市及文化发展的内在联系去探索这个地方的历史与今天,以及联系两者的内在逻辑———发展之道。记得临别时候,台湾的学长开玩笑说“肖然,我在google上搜到过你写美国和新加坡的文章,不错哦,期待《胡步台湾》,帮我们台湾好好做做宣导喔!”
一股冲动,让即将再次暂别母校,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的我提笔疾书,不仅是为了铭记,也不仅是为了“宣导”,而是想通过个人对台湾这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的亲身体验为你,为我,为我们这代人的“中国梦”做一个小小的注脚。
历史将会印证:如果中国人可以在中国边陲的一个角落里创造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奇迹”,那么中国人又何尝不能让这种奇迹在中国的每一寸山河开花结果,欣欣向荣呢?
经济腾飞——寻迹国鼎学长
上个学期,在台湾,正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想念,我踏上了发现台湾的旅程。曾经,在台风将至、小雨淅沥的午后,我撑着一把因为风力所击严重变了形的伞,走过李国鼎先生位于台北市中心的故居。庭院深深,高墙仡仡,这栋老式日本建筑笼罩在“暴”
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中,显得愈加神秘而让人心生敬畏。当初,也同样是在台湾经济和产业发展面临停滞的风雨困局中,我的这位南京同乡兼东大校友国鼎先生挺身而出,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塑造了台湾奇迹,成为上世纪整个六七十年代世界为之瞩目的明星。
以致今天的美国哈佛大学专门设有“李国鼎讲座”,邀请世界各地的博学鸿儒共襄学术盛世,斯坦福大学更是将一个经济学的校区命名为“国鼎苑”。
在作为小学弟和攻读经济类学科的我看来,台湾的经济起飞有两个重要的阶段,一个是“被国际化”中的工业化,另一个是“自主国际化”中的产业升级与海外转移,这关键的两步都出自李国鼎学长的设计。
畅想和追忆国鼎先生当时面对的台湾,资源贫瘠,地小人多,美国的“援助”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俗语有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想带领台湾走出山重水复的窘迫处境,不可能凭空建起万丈高阁,唯有因势利导,借助台湾已有的基础,将劣势转化为优势。
李国鼎深知,产业升级与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但是产业升级绝非越高越好,盲目的跨越式升级往往适得其反,设想一下你如何要求一个不会走路只会爬行的婴孩健步如飞地自由奔跑呢?因为产业升级而淘汰下来的劳动力可能无路可去,若是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安抚和帮助,极有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隐患,可谓是抽刀断水水更流。相反,如果能善加利用台湾人口多劳动力丰富这一比较优势,先发展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地少人多却要发展工业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定位在外销驱动上,将既可拓展海外市场,实现工业化;又可缓和内部矛盾,百姓各司其职,社会自然井井有序,还可为进一步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和民众支持。
于是,既可解决民生需求又能创汇的纺织工业成为了台湾在最初发展阶段的主打,同时,改革金融制度,吸引外资和华侨资本,也源源不断地为这一时期的台湾经济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与活力,为在台湾发展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创造了相当可观的条件。七十年代以来,这样的积累和坚持终于为台湾赢得了一个相对较好的发展基础。然而新的瓶颈也悄然而生,台湾不可能永远依靠来自外部世界的订单,甘愿做一个西太平洋上辛勤劳作却所获无多的“劳工”。或许就是在台北市泰安街2巷3号的这栋日式住宅里,李国鼎先生经过一番成熟的思考与酝酿,提出了台湾在新阶段的产业发展方略,中国人必须拥有自己动脑创造财富和价值的能力,于是一座座生机勃勃的工业园区在这个热带小岛上拔地而起。
有趣的是,大致同一时期在同样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一个同样姓李也同样精瘦的老者李光耀也作出了和李国鼎相同的决策,正如笔者在之前的《胡步新加坡》中提到的那样,通过设立出口加工区,创建科技园,华人在中国本土以外的地区第一次不用再唯唯诺诺于外国经济强权的颐指气使。有时,这种历史的巧合让你不得不在唏嘘赞叹之余感佩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文明滋养下迸发出的伟大气魄和惊人智慧。李国鼎的新政策成功吸引了分布于海外的华人科学家回到台湾投入如火如荼的科技研发和技术创新,使台湾开始摆脱人才外流的局面。整个七十年代到“民进党”执政之前,走出了传统加工业束缚的台湾,带着高附加值和高科技的双翼展翅高飞。
均衡发展——寻觅“南部”之路
晚年退居台湾的蒋介石为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取名经国和纬国,经天复纬地,这是两种维度,经纬相交确立了万物在这世界之上的位置。同样,要确定台湾的成就在中国历史发展乃至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坐标上的位置,除却对台湾产业发展的时间维度的追忆,更离不开对当代台湾产业和城市空间布局上的俯瞰。
坐在位于台南市的成功大学成功校区那株枝繁叶茂,蔚为壮观的大榕树下,我时常兴奋地想,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台湾全岛看作一个巨型的都市?如果这种富有浪漫气息的假设可以成立,那它确实是一个很符合现代产业化和城市化协同发展趋势的城市模型:台北是服务业高度集中的中央都会区或是CBD(中央商务区);新竹、台中是城乡接合部兼工业区,既拥有大城市的气氛和工业区的特质,却褪去了都市消费文化的浮躁和势利;而我所生活和学习的台南则是不折不扣的现代化郊区,以高新技术农业产业为主。这里生活便捷高质,却充满田园风光,空气里还依稀可嗅泥土的芬芳。
把这些城市功能区联系在一起的,在现代都市里通常是地铁系统。但在这座巨型都市中,则是台湾高铁:时速最高300公里,自北到南将台北和高雄两大重镇紧紧相连,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将台湾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当然台湾高铁囿于台湾狭仄的地理面积无法达到大陆高铁网所创造出的巨大社会和经济效益,然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次从桃园机场下飞机搭乘高铁去新竹的交通大学拜会友人,仅仅在飞驰的列车上待了十分钟就达到了目的地。这种有如搭乘地铁一般的便捷让台湾的高新技术、资本与信息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流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台北的西门汀,拿着地图的我曾被路边发放传单的商家误以为是南部来台北闯生活的嫩头青。在比较普遍的观点里,北部的经济发展优于南部,这种局面有点类似江苏省苏南和苏北的发展不均衡,或是整个中国大陆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落差。
如果说在交通层面上让北部的资本与资源在短期内快速撬动南部发展的一根杠杆是飞驰的高铁的话,那么教育产业的均衡化则成为在长远意义上带动产业布局差异明显的台湾南北协同发展的另一根卓有成效的杠杆。多年来在台湾的家庭中流传着“北台大,南成功”的说法,这里的成功指的便是笔者于此交流的成功大学。台湾当局每年将最多的经费分别投入这两所综合性大学的建设。台大的人文社科享誉华人世界,成大则偏重理工科发展,几十年来更是涌现出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等一批科学巨擘。以成大带动南部的科学和教育发展,并进一步推动南部的农业等传统弱势产业的现代化,使这根教育杠杆能真正可持续地撬动台湾相对落后的中南部,可谓是用心良苦。
作为台湾省最初的行政和文化中心,台南有郑成功和闽粤移民开发台湾所留下的城垣街肆及丰富的文化资产,孔庙里的石碑无声地叙述了清代台湾学子在全国科举角逐中的不俗表现。荷兰人留下的欧式建筑风格更是古代中国晚期对欧洲文明的一次不计前嫌的宽容和接纳。台南之于台湾,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蕴,我在成大读书期间,最热衷的事之一便是于周末的午后流连于那些精致优雅而安静的文化创意商店,或是在诚品书店听听每周不断的文化讲座,和仰慕的老师在充满异国情调的咖啡馆里讨论课堂上未尽的主题。台湾的南部用教育和文化的再升级给予我共鸣。在祖国大陆,西部大开发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教育的投入,大力建设中西部的高等学府,向中西部输送技术人才,我坚信中国人的智慧最终可以彻底改善区域发展不均衡这一人类发展中的普遍问题。
文化认同——寻找未来合魂
傍晚,夕阳尽染,窗外雄伟夺目的是富丽堂皇的圆山大饭店。这座很好地保留了中国古典宫殿造型和风格的台北地标性建筑巍巍然屹立于一片郁郁葱葱的青山之上,视线中几无高耸入云的摩登大厦相扰,它更给人无限视觉上的冲击,似乎足以让所有注目者为之振奋。可是,这团醒目的“中国红”此刻却无法带给我大脑的清醒。晨曦微露之时结束一夜的巴士颠簸从台南抵达台北,整个白天又马不停蹄地陪同访台的高中同学参观高度展现中华传统文明成就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如今正软绵绵地瘫在士林区的这所活动中心里。身体被因为很少穿着而显得并不合身的深黑色西装困住,热带夏日的空气中似乎又多了一份燥热,这一切都让我似乎有些后悔参加这个台湾大学主办的两岸华人青年论坛。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这段本应该因为疲惫而记忆模糊的经历在我的脑海深处烙下一个似将永恒的印记。
“分裂的时代,往往是文化经济蓬勃发展的‘世代’。大家不妨想想三国时代对整个中国文化的丰富性作出的贡献……”前面讲坛上的台大社科院院长试图向我们解释台湾在两岸分治的背景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作出的努力。然而,或许是因为双方所习惯的表达方式的不同,这种判断似乎容易让大陆学生产生联想。生性内敛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疲劳而无所顾忌,一股莫名的勇气油然而生,“院长及各位师长同学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东南大学的胡肖然,刚刚院长对三国的故事如数家珍,足见院长先生中国传统文化的修为,我希望补充的是《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句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想如今两岸已经分隔了蛮久了哦,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可以对中华民族团聚的未来有一个更美好的期待呢?”话音刚落,适才总显拘谨的氛围立刻被一阵欢乐的笑声打破。这笑声不分两岸,没有彼此,院长的脸上也露出一丝微笑,似乎也认可我对他的观点进行的这种有些俏皮但却认真的补充。我心中明白,刚刚两岸同胞这份真情流露的笑来自于彼此内心对于中华文化共有的那份尊敬与珍视。而这一点,或许是一条强韧的“化学键”,将两岸紧密相连。
也许在会上的发言让院长有些印象,会后院长再次问及我在大陆就读的学校。“1949年前的中央大学,李国鼎先生一生魂牵梦绕的母校!”我自信满满地回答。在台湾三个多月的生活让我深知李国鼎这三个字在台湾的地位与意义。悄悄瞥一眼面前这个学识渊博的台大教授,我分明能感觉到他神情的变化,那应当是一种肃然起敬吧,我暗暗揣测。
是的,台湾的所见所闻让我相信文化认同和各自努力的传承是今后两岸更紧密携手的合魂。
坐在经香港返回南京的航班上,略感无聊的我翻看起在台大政治系读书的好友送我留作纪念的书,扉页上竖着排列的是他用传统的繁体汉字题写给我的一段话。这个在民进党“去中国化”教育下成长的同龄人,却固执而骄傲地坚守着自己和家庭的“中国人”这一身份认同。正如我们那两次在台大东南角小咖啡馆里的谈话一样,他在这些文字中再次煽情地写下“过去我们两边的中国人走了两条不一样的道路,我总是希望大家能有更多机会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你来告诉我你这一路是怎么走来的,我也告诉你我这一路的辛酸和收获,那么将来总有一天,走了不同道路的两岸中国人再次团圆的时候,我们对彼此都能多一些包容和理解。”面对此情此景,我很难抑制自己的感动。的确,台湾走了一条不同于祖国大陆发展的产业化与城市化之路,这条台湾之路有曲折也有成功,我们这些交流学生的意义就在于沟通两岸的经验,总结彼此的教训,这样,在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上,我们可以少走些弯路,少跌些跟头,一马平川,勇往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