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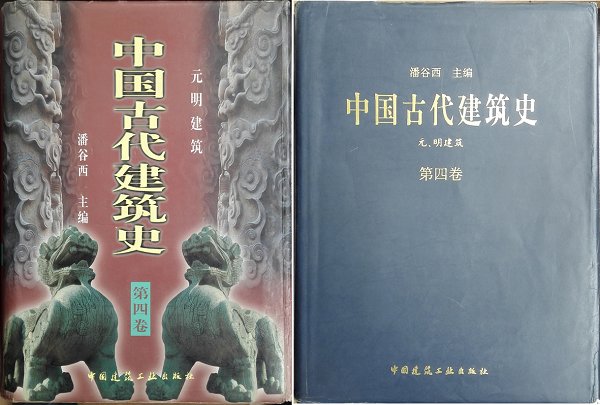
(接1312 期)在已经发行的6 个版本中,以第四版的修改变动最 大:
2000 年,根据国家教委及建设部“九五”高校教材规 划的要求,我们对第三版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修订与增 补,成为第四版。主要的变化有以下三项:
第一,古代建筑部分,根据近年来学术研究新成就,调 整、充实各章内容;增加了“建筑意匠”一章;并将“古代建 筑基本特征”的内容移于篇首作为“绪论”。
第二,近代建筑史部分更新对历史事实的评价,删除 了一些负面偏见;调整章节关系及内容安排。
第三,新增“第三篇现代中国建筑”整篇内容,弥补了 1982 年被出版社取消本篇所留下的遗憾。
当年二月,由主审陆元鼎先生在南京主持召开八校中 建史教师会议,对第四版书稿开展讨论,提出许多重要意 见。会后,对书稿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并根据审稿会意见增 编一份中国古代建筑图录,制成光盘,附于书后,作为教学 的辅助材料。光盘共收图片1300 余幅,多为作者历年积累 的幻灯片内容,也少量使用了公开发表的图片。光盘最初 定价每片30 元,经作者多次以减轻学生负担为由向出版 社建议,后改为每片10 元。出版社提出的精装、彩页本的 建议也未被作者采纳。
此次改版,调整了编写人员:乐卫忠和郭湖生两位作 者无意继续参加此项工作,改由朱光亚及陈薇二位继任。 其间又邀请武汉工业大学李百浩先生担任第16 章的编 写。近代建筑部分则全部由侯幼彬先生撰写。还根据出版 社转来的臧尔忠先生的《勘误》,复查、校勘了—次书稿内 容。
从第四版起,本书开始设立冠名主编人。
自2001 年6 月至2004 年1 月,第四版在两年半内共 卬 刷7 次,53000 册,平均每年21200 册。
2003 年,根据互联网上读者及建筑史学者所作中国 建筑教材“补遗与校勘”,对第四版作了一次认真校订,改 换封面,称为“第五版”。自2004 年1 月至2009 年8 月,五 年半共印刷15 次,187000 册,平均每年34000 册。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全国建筑学专业学生迅速增加的趋势。
2008 年,更换了第五版中已模糊不清的图片;对“现 代中国建筑”这一部分作了若干修改;封面换用天坛祈年 殿照片;并增加光盘中的图片200 余幅,是为第六版。
此前出版社负责此书的责任编辑为王玉容,从第六版 起由陈桦担任。
就专业学术价值而言,教材的编写,虽然主要是整理、 汇总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但我们并没有满足于此。我写 的那些部分,都是自己阅读史料、深入分析研究之后的结 果。比如按常规做法,建筑史的发展概况,会按编年史的体 例来写,而我在写发展概况的时候,抓住“发展”二字,也就 是仔细分析,看究竟有没有变化。有变化处加以强调,若无 变化,就不必多费笔墨。比如城市方面,历史资料浩如烟 海,影响一个城市基本状况的因素,有经济、政治、军事、文 化、艺术等各方面,非常之多,但那些都是背景性因素,着 重关注它们,就变成了一般的城市史。而我们是建筑学科, 着眼点在于城市的规划布局、城市的设计与建设,以及由 此而形成的城市形态,关注这些方面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 化,对于建筑学科的学生才有具体和现实的意义。我的目 标很明确,这本中国建筑史教材,不是写给搞历史、文化和 艺术的人看的,而是写给建筑学专业的学生看的,这个专 业的要求必须体现出来,他们大部分人将来是要做建筑师 的,所以我是侧重从设计、规划和建设的视角来观察、分析 和研究建筑史,以便开展建筑实践时能够汲取历史经验和 教训。这样做,对于我们这个专业更有价值、更实在。
应当说,《中国建筑史》教材的编写,是我开始独立承 担学术著作编撰的最早尝试,也基本上取得了应有的成 果。从此,我就开始专注于建筑历史与理论方面的研究,并 开始招收研究生,学术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真正投入进来之后,我就开始考虑,在中国建筑史的 学术领域里,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做。经过长期琢 磨,决心重新编写一部中国古代建筑史,希望能够全面、详 尽地反映中国建筑在历史上的发展状况和取得的成就。以 梁、刘二位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出版的主要还是简史。于 是,大约在1986 年前后,我就和郭湖生商 量,合作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写一 部能充分反映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和成就的 建筑史,题目就是《中国古代建筑史(多卷 集)》。这件事到现在想起来,仍是饶有兴味。 我们遭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方面拒绝了我们的申请,理由很 简单,他们说建筑史不属于自然科学。我们 就写信申辩说,建筑史不属自然科学,那么 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先生,不都是建筑历史 与理论方面的著名学者吗?不也都是中国科 学院的学部委员吗?于是他们终于同意并接 受了我们的项目申报。这件事也就在北京传 开了。此时,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那边提出 也要参加进来,并且还要由他们来牵头。为 说服我们,他们还请出了时任建设部副部长 的戴念慈,提议由他出任主编,他是中央大 学毕业的老校友嘛,而傅熹年和我任副主 编;同时提出,再由建设部拿出5 万元资助 本项目。郭湖生认为这样做不合适,明确表 示不同意,甚至我们东南大学当时的校长韦 钰闻听此事也很不满意。为此,我还应戴念 慈之邀去了一趟北京。我记得是在他的副部 长办公室谈了这件事。戴部长很客气,说希 望就此事征询我们的意见,我很直率地说:我们这边的老 师有意见,认为您本人主要从事建筑设计实践,并非建筑 史专家,担任这套丛书的主编,并不妥当。戴部长很明智, 听到我说这个话后,就自己退出了。
后来我校韦钰校长还专门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分 管土木建筑领域项目的关键人物那向谦来南京谈了一次, 似无结果。此事最终形成的状况是:项目获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将其列为“重要项目”,资助12 万元,建设部再资 助5 万元,经费管理权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戴念慈既 已主动退出,丛书就没有了总主编,而是 每卷分别有各自的主编。北京建研院方 面负责编写两卷,两晋、南北朝、隋唐、五 代是傅熹年主编,清代是孙大章主编。我 们这边也是负责编写两卷,汉代以前是 刘叙杰主编,元明时期由我主编。清华大 学负责宋辽金时期,由郭黛姮主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项目是有完 成期限要求的,我记得应该是3 年。但到 期之后,各项目组却拿不出稿子来。基金 委方面那向谦就对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说,那12 万元就算是给你们扶贫了!项 目组成员们当然也很不开心。后来,我主 编的元明卷于1993 年春最早交稿,为此 还专门开过一次审稿会,会议地点是在 梅庵。把北京方面的有关学者请过来了,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担任该从书责任编 辑的乔匀也来了。大家共同审阅初稿,提 出修改建议和意见,其实也没提多少意 见。最终的定稿是请陈薇送到北京去的, 给出版社和基金委各一份。那向谦拿到 稿子时对陈薇说,我要向你们道歉,不应 该说那样的气话。交稿之后,我们当然希望尽快出来。但乔 匀坚持还是要五卷一起出,这样一拖就是很多年。我们的 元明卷从1993 年交稿到2001 年出版,一共等了8 年。由 于没有总主编协调沟通,各分卷都是自己主编,相互之间 也没有往来。
现在看来,我们当时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也存 在失策之处。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把研究团队搭建得非常齐 整,甚至邀请北京方面来共同组织班子,情况也许会有不 同。当时的情况是,我们这边没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研究 机构,没有像刘先生那样的研究室,拥有完整的人才梯队 和充足的人力资源。我个人直接带领的研究力量非常有 限,只能依靠指导研究生做学位论文来逐年积累。另外,郭 湖生老师后来的退出,也是很大的损失。他不愿意做这种 扯皮的事情,如果他能够全程参与,那么我们这边在力量 上就更为强大了。
为什么要关注元明时期的建筑?其实,元代很短,主要 是明代建筑,而这一方面是过去已有研究比较薄弱的。于 是我就抓住明代建筑,把它作为一个时期,单独拿出来加 以深入研究,这在过去是不多见的。从选题角度而言,清代 距离今天过近;元代时间太短;宋辽金时期的建筑,营造学 社已搞过很多;而唐代遗留下来的实物太少。明代建筑,不 仅遗存实物较多,而且它的价值也很高,但过去却被忽视 了,认为它不及唐宋时期的建筑那样有价值,其实不然。另 外,人们常笼统地说“明清建筑”,将二者混在一起并提,事 实上他们说的只是清代建筑,明代建筑反而被掩盖了。其 实明代建筑更早,价值上也非常重要,清代建筑基本上是 直接继承了明代的,包括匠人和工程做法,是被清朝全盘 接收下来的。元朝的匠人到了明朝也照样继续建造宫殿, 而清初维修宫殿使用的都是明朝的工匠。所以,建筑上的 延续性,在官式建筑中表现得很充分。而官式建筑的变化 其实很缓慢,并不是以朝代来划分的。比如清代乾隆年间 有了较大变化,那时建筑非常兴旺。凡是非常兴旺的时期, 都有可能发生明显变化。它只有在技术上有了充分发展, 才会把前面的东西改变掉。所以,建筑发展变化的划分往 往是以高潮发生的时间点为依据的,和王朝更换并不一定 直接关联。
既然已经认定方向,我就没再犹豫。通过指导研究生 论文,对明代建筑进行了长期的、持续的研究。比如,杜顺 宝做的是明代皖南石牌坊;朱光亚做的是明代江南大木 作;丁宏伟做的是明代江南祠堂;张泉做的是明代南京城; 汪永平做的是明代的琉璃和家具;陈薇做的是明代江南建 筑彩画;张十庆和董卫做的是明代的村镇;龚恺做的是明 代无梁殿;郭华瑜做的是明代官式建筑大木作,等等。就这 样一路走下来,我们在《中国古代建筑史·元明建筑》中发 表了大量根据第一手资料做出的描述、分析和判断,使明 代建筑的历史面貌焕然一新。
由于在“多卷集”的研究过程中,对明代官式建筑的研 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接下来就开始了“明代官式建筑 范式”的研究项目,但由于精力不济,这个题目只完成了大 部分基础性资料的调查、收集工作,没能最后完成。
除了明代建筑以外,我还对古代城市建设做过一些研 究,比如唐宋的苏州、元大都、明南京以及明代的府县城 等,虽然没有花太多力气,但也有不少收获。因为明代的地 方志书很齐全,如宁波天一阁所藏志书,我们主要是通过 对志书的资料收集、分类和整理,从中看出地方城市的建 设面貌和历史成就,这也是过去未被注重的一个方面。从 元大都的研究可以看出,以往认为《周礼·考工记》指导了 元大都的城市规划,其实是有些想当然的。我得出的结论 是,元大都的规划建设是因地因时制宜的产物,反映出汉 蒙文化的融合,具有它本身独特的创造性,而非套用古代 陈旧城市规划思想的结果。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