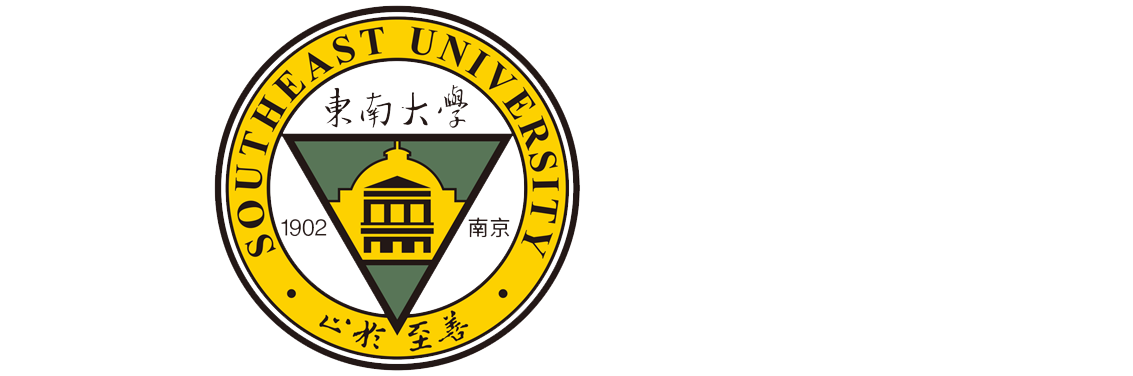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我有幸参加了中国9次核爆炸效应试验,这在当时是属于国家绝密,只有少数人员知道它的情况。随着时间的变迁,国家逐步解密,原来神秘的面纱逐渐被揭开。回眸过去在新疆大戈壁滩上参试核爆炸的情景,我总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仿佛就在昨天。
严格保密
我当初是从南京炮兵学校调到炮兵军事集训队的。来之前我问领导:“集训什么?”领导说:“我们也不知道,你去了就知道啦!”“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也没有多问。到了北京炮兵军事集训队,当时找我谈话的王队长说:“有项重要任务要你参加,十分保密,要求是‘三句话、十五个字’,记在脑子里、烂在肚子里、带进棺材里。”接着,办公室的姜参谋送给我一个小冊子,要我好好学习一下,翻开一看是《保守秘密的八项注意》:第一、不该问的秘密,绝对不问;第二、不该看的秘密,绝对不看;第三、不该说的秘密,绝对不说;第四、不该记录的秘密,绝对不记录;第五、不准在非保密本上记录秘密;第六、不准在私人通信中涉及秘密;第七、不准在公共场所和家属、亲友面前谈论秘密;第八、不准携带秘密材料探亲、访友和出入公共场所。经过学习后,领导告诉我,炮兵集训队是执行核效应试验任务的,任务很光荣,在国防科委直接领导下,代号叫“704”,接着分配了具体任务……至此,基本清楚了,由于首次执行任务,任务紧,要保密,我们便出发了。上级要求,这次参试人员一律不准回原单位和回家。当时思想斗争很激烈,为了执行光荣任务,为了保密,只好忍了。长途行军一到核试验场,音讯全无,一过就是四个多月。后来也就习惯了,我一走就是几个月,爱人带着两个孩子还要上班,十分辛苦,她也习惯了,支持我,为了执行保密的光荣任务!
行军宿营
从北京丰台火车站乘闷罐货车皮编组的专列,离开了北京。经过了七天七夜的闷罐车箱地铺生活,日夜兼程,通过“闷罐子”车厢的门缝里透过的光线,我们能得知是白天还是夜间,但究竟经过了几个昼夜,我们也说不清楚。路经南口、八达岭、包头、银川、张掖、酒泉、嘉峪关、鄯善、哈密,到达新疆吐鲁番大河沿21基地转运站,转乘汽车牵引火炮的解放牌卡车,又经过一天的颠簸路程,翻越天山、跨越戈壁,路经托克逊、库密什、乌斯塔拉。终于到达了马兰基地的工作生活区———红山,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当时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兼21基地张司令员接见了我们,他说:“你们都是国家的宝贝,搞原子弹试验要靠你们,你们都要做无名英雄,像无花果一样结出最香甜的果实,却不让人看见艳丽的花朵……”听了很受鼓舞。在基地又经过一段技术准备和保密检查后,我们又乘炮车向罗布泊核试验场区进发了。当时,进场的路面是沙石路面,车轮滚滚,尘土飞扬。沙石路面已被碾成了“搓板路”了,颠簸的路面使我们坐的炮车像风浪中的航船,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坐不能坐,站不能站,只觉得五脏肺腑都快被颠出来了,经过了一整天的颠簸,我们进入了核试验场区,罗布泊西北大戈壁。按照基地划分的区域,我们开始打帐篷,由于当地风大,固定帐篷很费劲,经过大家的努力总算打好了,帐篷里除了一张折叠桌就是几个行军床。白天,行军床上铺上图板,坐在马扎凳上就工作。晚上,放下图板就睡觉。宽广的戈壁滩,最缺的也最珍贵的是水。每天每人按定量分配,早晨洗睑的水放到晚上洗脚。水,是基地用运水车从上百里远的地方运来的,比汽油还贵。五、六月的罗布泊,已是早穿皮袄午穿纱的气候。晚上,盖着皮大衣在帐篷中听着大风吹得帐篷连同飞沙“呼啦啦”的响声,令人恐惧。白天,火热的阳光晒得戈壁滩滚滚发烫,帐篷里像蒸笼一样。开始每天吃罐头、压缩饼干,喝汽车兵从上百公里以外运来的带苦味的水。工作的环境干涸、冷漠、艰苦,但是我们的心是温暖的。看着这片广阔无垠的戈壁滩感慨万分,四百多里没有人烟,面积10多万平方公里,这是一个充满神秘的地方,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一个震惊世界的地方。
“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不怕困难,不畏强梁;任凭天公多变幻,哪管风暴沙石扬。头顶烈日,明月作营帐。饥餐沙砾饭,笑谈渴饮苦水浆。”这是张爱萍将军在1964年9月27日为核试验参试部队所作,很快21基地春雷文工团把词作谱写成队列歌曲,《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在参试部队中传唱,这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爆前布点
中央专委会主仼周恩来总理提出“在效应试验上,要摸清楚在空中、地面各种条件下杀伤和破坏的威力半径。总之,凡是通过试验应该得到的数据和资料都要得到。中国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我印象最深的的核爆,是1967年6月17日,新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这次效应试验,人员之多,规模之大,可谓是空前绝后的。在靶心以西30公里范围内,沿着通京两侧布设了许多条效应试验线,主要有:汽车线、飞机线、火炮线、坦克线、雷达线、楼房线、粮仓线和动物线等。除此之外,还有:一座铁路桥上停靠着一辆火车头、一个避风港内停了一个舰艇模型、枪支弹药、服装布匹、种子粮食,可谓是应有尽有,这简直就是一个盛大的露天博览会。我所在的“704”负责火炮线及炮兵分队在核爆条件下的战术行动试验,本人具体负责的试验项目,炮兵工事防护,在不同距离,几种工事內外均设置了狗、兔代替人员并设置了防冲击波、光辐射、早期核辐射和放射性沾染的侧量仪器。试验项目均在核爆前准备完毕,并多次参加基地指挥部全场联试,不断査缺补漏,做到万无一失。在比期间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防护训练,它是一种特殊的艰苦而确保安全的训练。开始防护服是胶质的,橡胶味很浓,又不透气,穿上训练一次,可从防护靴内倒出半罐头盒汗水,体重下降。在训练中,我和同志们都经历了头晕、呕吐、脑胀、口渴、憋气,摘掉面具后连饭也不想吃。但是我们为了核爆后进沾染区工作,回收取样,再难受也得克服,当时单位开展学英雄活动,同志们越练越来劲,经过多日反复训练,均达到了过关标准坚持4小时。这真是”防护训练有万难,学习英雄就过关”。
观察核爆
1967年6月17日早晨,我们参试人员被安排到远离爆心的白云山一带观察点,每人发了一副伸手不见五指的高倍密封墨镜。当听到报时员“零前十分钟”的口令时,装载着氢弹的“轰-6”飞机轰鸣着从我们头顶的高空飞过,我急忙把墨镜扣在双眼上,随着“10、9、8、7、6、5、4、3、2、1———起爆”的那一刻,墨镜里一片白光,脸颊像被近在面前的火焰烤了一下,火辣辣地发烫。
白光过后的五分钟,我按口令摘下墨镜,只见远远的天边,红色的火球在翻滚,巨大的蘑菇云在升腾,在蓝色天空中,蘑菇云是那么洁白无暇,像一朵白白的棉花,开在一个欲张的白色太阳伞上。蘑菇云很快扩散到高空,我们由平视变成仰视。只见蘑菇云升起,但听不到氢弹爆炸的响声。我身边的申江河指导员正低头看手表,他用山西口音大声喊到:“十五分钟了,把嘴张开!”我不知所措地张开嘴,看到前方戈壁滩上像风刮起的一层飞扬的沙土,滚着波浪向我们面前推来。当看到的沙土波浪冲到眼前时,一声巨大的声响震耳欲聋,耳鼓发痛,声波像一堵墙推着我,我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好强大的冲击波啊!这是氢弹的冲击波!
我们欢呼!我们雀跃!
我们高喊着:“成功了!”“毛主席万岁!”“祖国万岁!”
回收取样
零后(核爆后)约一小时,我们穿上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坐上特殊编号的回收取样的汽车,浩浩荡荡地向爆心开进。最前面由装有α射线剂量探测仪的防化装甲车开道。进入沾染区后,在一个标有“安全检查站”的装甲车旁停车,接受防化兵对每个人的防护服和防毒面具的检查,每人发一支剂量笔,佩戴在防护服外的上衣口袋上。在沾染区前进,道路两边的电线杆在燃烧,穿着陆、海、空军装的假人在燃烧,用做效应试验的飞机、汽车在燃烧……越临近爆心,燃烧的物品越多、破坏的程度越大。坦克被掀翻,汽车四轮朝天,砖房成了一片瓦砾,木屋成了一片火海。参加效应的铁道兵的火车头、海军的鱼雷快艇、空军的歼击机东倒西歪,都成了被烧焦的残骸。临近爆心,所有的地面装备无一完好,眼前尽是火焰和废墟。我所担负的试验项目,炮兵工事內外设置的狗、兔,在距爆心15公里以內均遭到了不同等级的杀伤。
在零后三个多小时,我们乘坐的汽车到达了爆心,巨大的蘑菇云已经扩散东去,前方的路已无法通行了,爆心方圆一、两公里的地面已被烧灼成玻璃体,像一块巨大的玻璃片铺在爆心地面上,在正午的阳光下反射着强光,形成“上有太阳,下有反光”的景象,令人不能抬头,也不能低头,只能眼睛平视远方,盲目地向前迈腿,只听脚下踩踏玻璃的破碎声“咔喳、咔喳”作响,厚厚的玻璃体下是松软的沙土,踩下去像踏空一样,一步一步,非常艰难。
零后的三个多小时,玻璃体还在散发着炽热,隔着厚厚的防护鞋还能感到脚底的热量,像踩在烧热的铁板上一样发烫。同车下来的人,因为都穿着防护服、戴着防毒面具,都一个模样。在防毒面具里只能听见自己“呼剌,呼剌”的喘气声,而听不见外界的声音,互相说话谁也听不到,只能打着手势,像哑巴一样。因为是在爆心,不能久留,我们只在爆心的边缘走了几步,就很快返回车上,按防化分队设置的路标,从另一条洗消路离开硝烟弥漫的爆心,又开了两个多小时,到达了安全边界。在那里,我们终于可以摘下防毒面具,脱下防护服和防护鞋,经防化分队的剂量检测,我的剂量指数为零。安全顺利地完成了任务,那一刻,我如释重负,轻松地大口呼吸。回到驻地很快整理回收资料,准备回京分析上报……晚上,我们在帐篷里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新闻公报》“我国在西部地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每个人都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好多人的脸上都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我感到光荣!我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