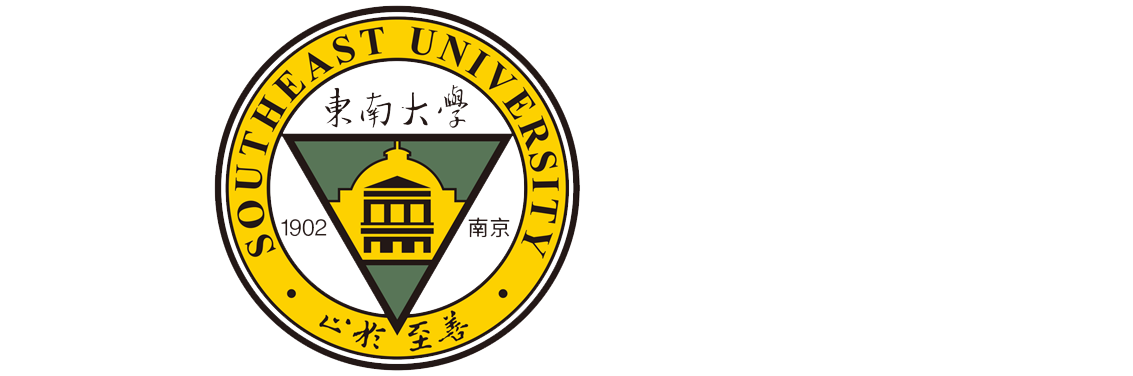1、记者:卢爷爷,请问您什么时候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对南京印象如何?
卢国纪:我1948年8月毕业于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在国立中央大学西迁重庆的校区上过三年学,在南京四牌楼校区上过一年学。我对南京的印象特别深。南京的行道树很好,绿树成荫,走在上学的路上,觉得南京太美了。2004年去过一次南京,可惜现在不行,因为2005年摔了一跤,造成骨折,走路不太方便,没有办法去南京了。我对南京有非常深的感情。
2016年,南京决定授予我南京市荣誉市民称号,因此我非常高兴。我请你们代我问候南京市的领导和全体人民。希望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也希望我的母校(现在的东南大学)越来越好。去年,南京市委书记和市长亲自签名,给我写了一封信,认为我永远都是南京市市民。
我一直觉得我有两个故乡,第一个是重庆,第二个就是南京。这两个故乡我都非常热爱。任何一个人都爱故乡。当年,我是从水路坐船从重庆沿江而下到达南京,然后从中山码头步行到学校。在南京,我最想再走一遍的路就是经过山西路到四牌楼。我的姐妹们都在金陵大学念书,也是步行上学。我在这里还很怀念的是,在星期天和朋友一起到玄武湖划船,去电影院看电影,这些都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面。
2、记者:您还记得当时在学校里生活的一些情况吗?
卢国纪:记得。国立中央大学在重庆柏溪的一处偏僻的小地方建了一个分校。我一年级就在柏溪上课。上工学、理学都要学习高等数学,我免学,因为我都是考一百分。在柏溪校区的时候,由于我免学高等数学,所以星期六就有了空闲,我就坐船回到重庆家里,星期一下午有课,我就坐船回柏溪。当时民生公司的船,是木船,开得比较慢,我们叫做“地漂”。在柏溪上学,条件十分艰苦。我们住在很偏僻的地方,吃饭就在一个大石头上。但我觉得中央大学是很不错的学校。难怪我的父亲,在我报考的四个大学中一定要我去中央大学。前几个学校的成绩出来了,父亲不急不躁,他就一直等中央大学发榜,结果中央大学发榜了,我考了中央大学工学院第一名。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对中央大学有了深厚的感情。
3、记者:在淞沪会战时期,您的父亲卢作孚先生帮助国立中央大学大撤退,这段故事您能和我们讲解一下吗?
卢国纪:当时,罗家伦校长找到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当即确定第一个撤退的大学就是中央大学,然后是金陵大学。当时的秩序就是这样。他首先确定搬迁中央大学,因为中央大学当时是全国最高学府,所以必须把中央大学迁走。
4、记者:在宜昌大撤退的时候,您父亲在里面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能和我们讲讲吗?
卢国纪: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进出四川的通道就成了抗战的重要运输线。长江水道便成了进入四川最便利的路线,成了抗战期间贯通前后方最重要的“黄金水道”。而此时的宜昌情况十分危急,处在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因为从上海、南京、苏州、武汉等地匆忙撤出的工厂设备已陆续集中在此,南京撤出的政府机关、各地要撤到后方的学校也集中在此。
1938年,日本军队占领了武汉,10月24日武汉沦陷。我的父亲在10月22日将最后一批机械设备装上轮船,然后坐飞机飞到宜昌。
他到宜昌一看,一片混乱,三万多等待撤退的人民群众已经堵塞在宜昌街头,九万多吨机械设备包括重工业、轻工业、兵器工业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堆在江边。这些机械设备都是国家的命脉,一旦落入敌军手中,后果不堪设想,而那时宜昌只有四十多天就到枯水季节,一旦到了枯水季节,大船不能走,就完全不能撤退了。民生公司船只有限,要把大量的货物运到重庆,采用通行的办法耽误的时间太长,必须加强组织,扩大运力。我的父亲于10月22日到达宜昌的当天晚上连夜召集相关人员,开会商讨撤退办法,采取在枯水季节使用的“三段航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否则来不及撤退。“三段航行”的意思是最重和最重要的机械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历时六天;不太重要的机器设备运到万州就卸下来,再用其它船只转运,时间缩短一半,只要三天;更不重要的运进三峡就卸下。所有进程均由我父亲一人指挥。他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日日夜夜片刻不离,通宵都在指挥。四十天过去了,宜昌的人民群众和机械设备全部运走了。
运走的机械设备很快在重庆四周投入使用,对巩固工业基地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重新生产的武器被运往前线。宜昌大撤退被誉为“东方的敦刻尔克”。
撤退之后,1939年初,宜昌沦陷,中国军队正在湖南与日军展开长沙大会战。没有后勤部队,如何作战,我的父亲亲自到现场探查,不到一个月就动员民工开始了水陆联运。水陆联运就是民生公司的船把军队、军火、粮食运到港口,然后民工将东西背上山,装上汽车运送到前线,从而确保中国军队在长沙大会战取得胜利。
从1939年起,日军开始集中轰炸民生公司的轮船。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民生公司的主力船只被炸沉炸毁16艘,船员被炸死117人,因工致残76人。但民生公司职工仍然勇往直前,不怕牺牲,谱写出了壮丽的诗篇。1940、1941年两年,我的父亲全力修建从川西到川东的公路,以期将川西的物资运到重庆,加工后以供应前线的需求。1941年的夏天,我的父亲被诊断出患有心脏病,因为心脏间歇性跳动,医生建议必须卧床休息,而重庆的存粮却只够两个月,一旦粮食断绝,不但重庆将引起混乱,前方也没有粮食。就在这时,国民政府让我父亲担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我的父亲不顾身体,毅然接受职务。
建国初年,毛泽东曾对黄炎培说: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有四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5、记者:您父亲在中央大学西迁的这段经历在以后的日子里有跟您提过吗?
卢国纪:他不提。因为他从来不将他做过的那些贡献跟我们讲,觉得这是他应该做的。
6、记者:您如何看待国立中央大学从南京迁到重庆?
卢国纪:是这样的,国立中央大学迁到重庆我了解并不多。因为那时我才上中学,我的父亲很少讲起这件事。他在家里面从来不讲。直到考大学的时候,我的父亲要我一定要报考中央大学,我才了解到中央大学,并服从了他的意见。我的父亲不幸去世后,我就一直怀念父亲,也一直怀念中央大学,也怀念南京。
7、记者:当年飞机来轰炸时,您对躲防空洞的记忆还有吗?
卢国纪:我的父亲通宵都在工作,不回家,后来因为日本飞机晚上也轰炸,重庆实行灯火管制,他晚上就不去公司了。我的父亲有非常高的爱国热情,有一次,我们没有进入防空洞,日本飞机来轰炸,我们就到重庆郊区的一个崖上,全家人坐车到山崖上,在皎洁的月光之下,金黄色的稻田旁边,我的父亲给我们讲学习,讲工作。最后,突然问我们:“世界上什么花最香?”我们都说稻花。我的父亲笑了。因为稻子熟了,老百姓有粮食吃了。他心里想的,全是老百姓。
1941年,我和我的哥哥跟着我的父亲一起去成都,在中途,我的父亲停下来,准备到一个老朋友的糖厂去。我父亲的老朋友带我们看甘蔗进机器到变成白砂糖的过程。出了厂房,我的父亲就跟我和哥哥说:“你们知不知道厂长的情况,他高中毕业后到美国学习制糖,他完全可以到上海这些地方开糖厂。”那时我的父亲是四川省的建设厅厅长,我的父亲请他到四川来,四川那时是一个没有任何工业的城市,那个厂长却来了。
从厂里出来,我的父亲就对我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一个人要在工作上和人比,不要在生活上和人比,即使做一个邮差,也要做世界上最好的邮差。”这段话,我一直记在脑海里。我在民生公司也常常讲。
我在民生公司座谈会上还说了一句话:“既然重庆市委让我来恢复民生公司,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