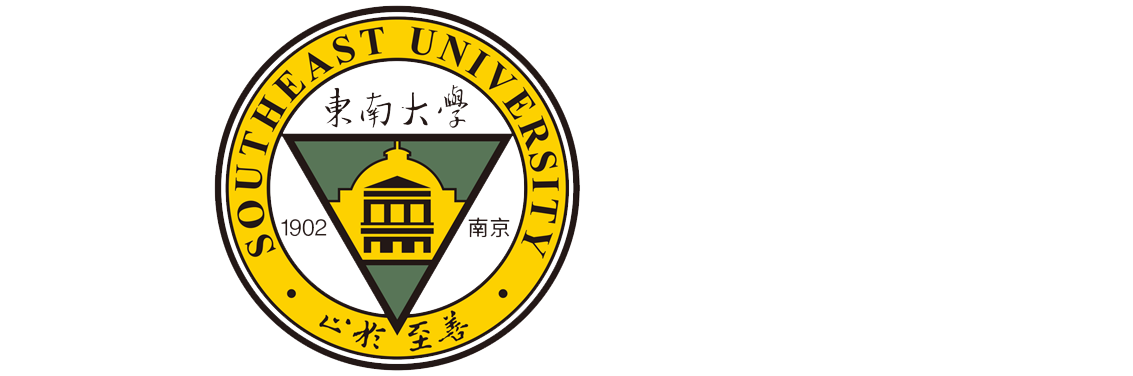小时候我对树的兴趣远远大过花。在漫长的夏日午后,我搬着小板凳在窗台上凝望着窗外的树,看着树叶变幻着风的形状,常常觉得每片树叶都是一个跳舞的小人,他们正在举行盛大的夏日舞会。我听得懂树木和风的悄悄话,以及各种鸟语,我看到树木露出微笑或忧伤的表情,我也跟着欢乐、悲伤和舞蹈。那时候,我是孤独的,经常被双职工的父母锁在家中的小孩。
初到南京的时候,有个朋友,是南京土著,骑车走在中山东路上,他告诉我,南京市主要街道有20条,其中16条是以“法桐”作为行道树的。在中山东路,梧桐有难以置信的六排。每到夏天,火炉南京,赤日炎炎,走在“法桐”大道上,却是绿荫成廊,遮天蔽日,轻风拂面,行人、骑自行车者、驾驶汽车者在此经过,简直是一种享受,下雨的时候都不用撑伞,自然形成了一道绿色长廊。听着南京人带点自豪感的讲述,我眼里的南京仿佛侯孝贤电影的镜头,悠长、缓慢、从容、慢慢的长镜头,一点点拉近,枝繁叶茂的梧桐树仿佛沧桑的老人,遒劲的枝条在空间互相呼应,道路的尽头恰是长满了青苔的中山门,春天迎春花从城墙上覆盖下来,像是一个黄色的屏风,隔开了瑞金路市井的繁华热闹,那一面便是紫金山的沉静幽深。
然后,我一下子爱上了南京的梧桐树。
住在苜蓿园附近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要开车进山,炎炎夏日,一进紫金山便是冠盖如伞,遮天蔽日,两排苍劲的梧桐如同列队的士兵,庄严肃穆又亲切哀戚,仿佛在这里站了千年,并不为与你相遇,只是命中注定要站在这里。有一次台风到来,晚上我执意进山,看看这些梧桐树,巨大的树冠在风的作用下发出魔鬼般的啸叫。山上车都难以正常通行,被风刮断的树枝尸横遍野,叶片散落,整座山充满悲伤的气息,但隔几日再去,梧桐树又恢复了原样,仿佛从未受过蹂躏,就像历尽劫难的南京人,再次站起的时候,总是更加豁达和宽容。
南京的高校也都是类似的格局,一进校门,两排巨大的梧桐,诉说着校史的悠久,《少年班》、《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等电影都喜欢在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取景,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道路两旁的梧桐树带来的历史感和沧桑感。古人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个叶,指的就是梧桐叶。最喜欢秋冬季的校园,大礼堂前的涌泉池依然涨一池绿水,金黄的梧桐叶如手掌一般轻轻飘落,浓艳的绿和金色的黄,有着一种庄严的美。晚上在校园散步,月光从梧桐枝叶的缝隙中射过来,又仿佛李煜的“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承载很多不为人知的少年心事。梧桐被古人视为“灵树”,其生也不凡:“扶桑、梧桐、松柏,皆受乞淳矣,异于群类者也。”素有凤栖梧桐之说,连宋词都有《凤栖梧》的词牌名,柳永的凤栖梧中“拟把疏狂图一醉”是很出名的调子。《大雅·生民之什·卷阿》有“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之句。凤栖东南,与子携归。
一入秋,外地的朋友纷纷问我南京的秋叶黄了没有,明孝陵的神道此时已一秒变金陵,千秋万代亘古不变的样子……短短六百米,棕黄的法国梧桐,橙红的榉树、枫香,橙黄的乌桕,常绿的圆柏,灿黄的马褂木、银杏、无患子……这是紫金山秋色的进阶之路。石象路神道由东向西北延伸,狮子、獬豸、骆驼、象、麒麟、马,巍然肃立。某一个秋雨降温的夜晚,开车经过一个梧桐小道的时候,忽然风至,大片的梧桐叶如蝴蝶纷飞,车灯打在叶上,顿时金色如炬,仿佛瞬间重生,车在飞舞的树叶中穿行,令人敛声…我去过很多地方,但再没有一座城市让我一见就想留下来。南京,仿佛是我前世的乡愁。而无论去到哪里,我都会知道,南京,有一棵想我的梧桐树,等我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