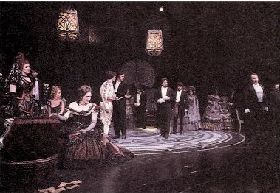
“一个月里有25天她带的是白色的山茶花,另外5天则是红色的;可谁也不知道这样颜色变换的原因。”我们无从知道,或许我们也不需要知道。我们知道的只是,这朵娇艳欲滴的茶花,凋零地那样惨烈而美丽,那样的不可一世。
放下《茶花女》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自己是颤抖的,颤抖的不是握着茶杯的手,而是早已被震撼的心灵。我不知道几百年来有多少人为它同情和伤心地落下了眼泪,但它确实让我长久不息地难过和伤感着。
我几乎是声嘶力竭地问着一个同样的问题:是什么扼杀了绽放在墙角的茶花呢?
起初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忿忿地看待迪瓦尔先生———也就是阿尔芒的父亲的出现。因为他的出现,年轻幸福的男女主人公离开了承载着他们一生梦想的布吉瓦尔;因为他的出现,玛格丽特的美梦如幻彩的气泡一样触之即破;也因为他的出现,让经久不衰的真爱在此刻的巴黎变得混沌不堪。
然而确实是这样吗?我深深地扪着心口……其实这个正直的老先生只是阻挠伟大爱情的一块绊脚石,或者说只是扼杀茶花的一样凶器,真正的凶手,是阿尔芒的虚荣与猜疑。
二十四岁的阿尔芒在巴黎读完大学取得了律师资格之后,并没有立刻去找一份工作,而是“把文凭放在口袋里,也让自己过几天巴黎那种懒散的生活。”在他不间断的寻欢作乐之中他邂逅了名妓玛格丽特。不可否认,他是十分喜欢玛格丽特,实际上,他也确实极度爱着她。可是他那多猜忌的性格,却一开始就注定了这场悲剧的到来。阿尔芒是多情的,他为了她神魂颠倒,在每个黑夜里孤独地期待黎明的到来;阿尔芒是妒忌的,他看到伯爵进入了她的房间就仿佛看见一把尖刀狠狠地在自己心上扎;阿尔芒是软弱的,他无力也没有勇气去追求他们苦苦追寻的幸福,而是在父亲严厉的目光下彷徨失措;阿尔芒是不幸的,只有他才是火红茶花下真正的悲哀,而玛格丽特却可以美丽地死去,可以安静地净化灵魂。
一个人心中没有爱情的时候可以满足于虚荣,但是一旦有了爱情,虚荣就变得庸俗不堪了。
阿尔芒本可以成为玛格丽特生命中的明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彼此牺牲过。然而他的虚荣与猜忌摧毁了一切美好。因为他并不理解玛格丽特,他如此偏激地认为自己受骗了,他自以为地觉得自己是这个故事最无辜的人,于是他不惜寻求一切机会进行报复,折磨她越深,就越能满足他的虚荣心。他在玛格丽特的哀求中虚伪地放声大笑。但他却悲哀地忽视了真爱所应有的真诚与信任,他带着满腔的恨去做了一次一辈子为之后悔的长途旅行。
而玛格丽特没有,她没有悲哀。她并不后悔所有的选择,她深信当阿尔芒知道真相的时候,她会在他的眼中显得格外崇高,虽然这是她死后的事情了。玛格丽特是一个坚强的姑娘,她一个人面临着死亡,她又如此善良,不愿让他看到自己死亡前的痛苦。她一生最快乐的时光是阿尔芒给予的,但她一生最痛苦的时光同样也是阿尔芒给予的。正是因为阿尔芒,她的生命才有了光彩。也正是因为阿尔芒的出现,使她承受了比之以前更深切百倍的痛苦。
或许再退一步想,优雅的茶花本就不应该生存在漆黑狭窄的角落里,就想善良的玛格丽特本就不应该生活在充斥着懒散与虚荣的巴黎昂坦街一样。在没有阳光只有糜烂的墙角里,茶花的命运只剩下凋零;在没有真诚只有挥霍的巴黎,玛格丽特的世界只剩下天主。
是的,玛格丽特并不是个一个完全的悲剧人物,至少,她得到了真爱,她的灵魂得到了净化。贵妇人们只看到了她生活的奢侈和物质的享受,却不知道她高尚的情操也是自己所望尘莫及的。在这个只是表面华丽,而内心里丑陋的现(下转六七版中缝)实里,人们彼此互相欺骗,用虚伪遮掩在世界里,她的存在是必然的,她的命运更是无法逆转的。或许连她自己都在厌恶这一切。奇怪的资本主义上流社会的人们,明明鄙视放荡的妓女,却又要逼良为娼。如果玛格丽特没有生在这样一个肮脏、虚伪、残忍的资本主义时代,或许她就是圣母玛利亚。可惜那样的社会,那样的时代,或许连圣母也会被玷污。而在玛格丽特被玷污的躯壳下,顽强而又圣洁的灵魂正是我们这些读者暗暗哭泣的原因。
墙角里钻出一朵茶花。一个阴冷、黑暗、潮湿、没有阳光的墙角,糜烂是它的养料。然而,这茶花却比别的茶花,甚至别的任何一种花都美丽,美得脱俗,美得惊人,美得如痴如醉。可凡是花都是向往阳光的。努力、再努力一点,在茶花碰触到阳光那一刹那,在它因阳光的滋润而娇艳欲滴的那一刹那,无情的风折断了花枝,让它又倒在了阴冷的角落,无力再爬起,再去触摸那伸手可及的阳光。上帝是仁慈的,为了弥补命运对它的不公,没让它凋零后再死,而是让它保持着美貌离开了世间。
一个叫小仲马的诗人经过,他怜悯地乞求上苍:希望那已死去茶花再次从泥土中萌芽、重生的时候,远离那阴暗的墙角,能每天和阳光为伴,即使不再那么美丽,也不要再重复前世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