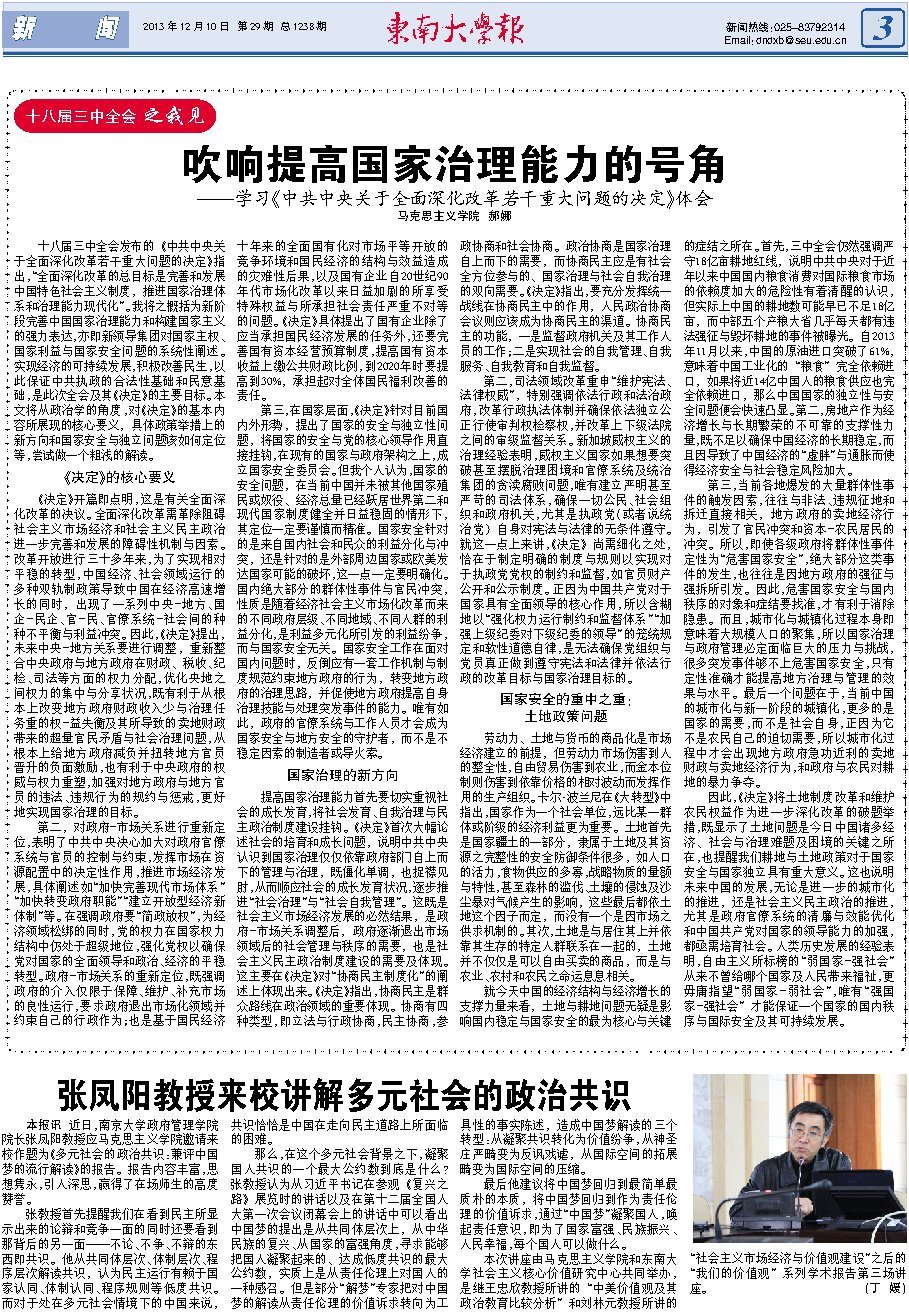
标题导航
- 张凤阳教授来校讲解多元社会的政治共识
摘要: 本报讯近日,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张凤阳教授应马克思主义学院邀请来校作题为《多元社会的政治共识:兼评中国梦的流行解
- 吹响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号角
摘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我见
吹响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号角
———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体会马克思主义学院郝娜
期次:第1238期
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将之概括为新阶段完善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和构建国家主义的强力表达,亦即新领导集团对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问题的系统性阐述。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积极改善民生,以此保证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和民意基础,是此次全会及其《决定》的主要目标。本文将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决定》的基本内容所展现的核心要义,具体政策举措上的新方向和国家安全与独立问题该如何定位等,尝试做一个粗浅的解读。
《决定》的核心要义
《决定》开篇即点明,这是有关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全面深化改革需革除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障碍性机制与因素。
改革开放进行三十多年来,为了实现相对平稳的转型,中国经济、社会领域运行的多种双轨制政策导致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一系列中央-地方、国企-民企、官-民、官僚系统-社会间的种种不平衡与利益冲突。因此,《决定》提出,未来中央-地方关系要进行调整,重新整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财政、税收、纪检、司法等方面的权力分配,优化央地之间权力的集中与分享状况,既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少与治理任务重的权-益失衡及其所导致的卖地财政带来的超量官民矛盾与社会治理问题,从根本上给地方政府减负并扭转地方官员晋升的负面激励,也有利于中央政府的权威与权力重塑,加强对地方政府与地方官员的违法、违规行为的规约与惩戒,更好地实现国家治理的目标。
第二,对政府-市场关系进行重新定位,表明了中共中央决心加大对政府官僚系统与官员的控制与约束,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进市场经济发展,具体阐述如“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在强调政府要“简政放权”,为经济领域松绑的同时,党的权力在国家权力结构中仍处于超级地位,强化党权以确保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和政治、经济的平稳转型。政府-市场关系的重新定位,既强调政府的介入仅限于保障、维护、补充市场的良性运行,要求政府退出市场化领域并约束自己的行政作为;也是基于国民经济十年来的全面国有化对市场平等开放的竞争环境和国民经济的结构与效益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以及国有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以来日益加剧的所享受特殊权益与所承担社会责任严重不对等的问题。《决定》具体提出了国有企业除了应当承担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外,还要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到2020年时要提高到30%,承担起对全体国民福利改善的责任。
第三,在国家层面,《决定》针对目前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国家的安全与独立性问题,将国家的安全与党的核心领导作用直接挂钩,在现有的国家与政府架构之上,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但我个人认为,国家的安全问题,在当前中国并未被其他国家殖民或奴役、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和现代国家制度健全并日益稳固的情形下,其定位一定要谨慎而精准。国家安全针对的是来自国内社会和民众的利益分化与冲突,还是针对的是外部周边国家或欧美发达国家可能的破坏,这一点一定要明确化。国内绝大部分的群体性事件与官民冲突,性质是随着经济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而来的不同政府层级、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利益分化,是利益多元化所引发的利益纷争,而与国家安全无关。国家安全工作在面对国内问题时,反倒应有一套工作机制与制度规范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转变地方政府的治理思路,并促使地方政府提高自身治理技能与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唯有如此,政府的官僚系统与工作人员才会成为国家安全与地方安全的守护者,而不是不稳定因素的制造者或导火索。
国家治理的新方向
提高国家治理能力首先要切实重视社会的成长发育,将社会发育、自我治理与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挂钩。《决定》首次大幅论述社会的培育和成长问题,说明中共中央认识到国家治理仅仅依靠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的管理与治理,既僵化单调,也捉襟见肘,从而顺应社会的成长发育状况,逐步推进“社会治理”与“社会自我管理”。这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政府-市场关系调整后,政府逐渐退出市场领域后的社会管理与秩序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需要及体现。这主要在《决定》对“协商民主制度化”的阐述上体现出来。《决定》指出,协商民主是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协商有四种类型,即立法与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和社会协商。政治协商是国家治理自上而下的需要,而协商民主应是有社会全方位参与的、国家治理与社会自我治理的双向需要。《决定》指出,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作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则应该成为协商民主的渠道。协商民主的功能,一是监督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二是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
第二,司法领域改革重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特别强调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改革行政执法体制并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并改革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审级监督关系。新加坡威权主义的治理经验表明,威权主义国家如果想要突破甚至摆脱治理困境和官僚系统及统治集团的贪渎腐败问题,唯有建立严明甚至严苛的司法体系,确保一切公民、社会组织和政府机关,尤其是执政党(或者说统治党)自身对宪法与法律的无条件遵守。就这一点上来讲,《决定》尚需细化之处,恰在于制定明确的制度与规则以实现对于执政党党权的制约和监督,如官员财产公开和公示制度。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具有全面领导的核心作用,所以含糊地以“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的笼统规定和软性道德自律,是无法确保党组织与党员真正做到遵守宪法和法律并依法行政的改革目标与国家治理目标的。
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
土地政策问题
劳动力、土地与货币的商品化是市场经济建立的前提,但劳动力市场伤害到人的整全性,自由贸易伤害到农业,而金本位制则伤害到依靠价格的相对波动而发挥作用的生产组织。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指出,国家作为一个社会单位,远比某一群体或阶级的经济利益更为重要。土地首先是国家疆土的一部分,隶属于土地及其资源之完整性的安全防御条件很多,如人口的活力,食物供应的多寡,战略物质的量额与特性,甚至森林的滥伐、土壤的侵蚀及沙尘暴对气候产生的影响,这些最后都依土地这个因子而定,而没有一个是因市场之供求机制的。其次,土地是与居住其上并依靠其生存的特定人群联系在一起的,土地并不仅仅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而是与农业、农村和农民之命运息息相关。
就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来看,土地与耕地问题无疑是影响国内稳定与国家安全的最为核心与关键的症结之所在。首先,三中全会仍然强调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说明中共中央对于近年以来中国国内粮食消费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度加大的危险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但实际上中国的耕地数可能早已不足18亿亩,而中部五个产粮大省几乎每天都有违法强征与毁坏耕地的事件被曝光。自2013年11月以来,中国的原油进口突破了61%,意味着中国工业化的“粮食”完全依赖进口,如果将近14亿中国人的粮食供应也完全依赖进口,那么中国国家的独立性与安全问题便会快速凸显。第二,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与长期繁荣的不可靠的支撑性力量,既不足以确保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而且因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虚胖”与通胀而使得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风险加大。
第三,当前各地爆发的大量群体性事件的触发因素,往往与非法、违规征地和拆迁直接相关,地方政府的卖地经济行为,引发了官民冲突和资本-农民居民的冲突。所以,即使各级政府将群体性事件定性为“危害国家安全”,绝大部分这类事件的发生,也往往是因地方政府的强征与强拆所引发。因此,危害国家安全与国内秩序的对象和症结要找准,才有利于消除隐患。而且,城市化与城镇化过程本身即意味着大规模人口的聚集,所以国家治理与政府管理必定面临巨大的压力与挑战,很多突发事件够不上危害国家安全,只有定性准确才能提高地方治理与管理的效果与水平。最后一个问题在于,当前中国的城市化与新一阶段的城镇化,更多的是国家的需要,而不是社会自身,正因为它不是农民自己的迫切需要,所以城市化过程中才会出现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卖地财政与卖地经济行为,和政府与农民对耕地的暴力争夺。
因此,《决定》将土地制度改革和维护农民权益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破题举措,既显示了土地问题是今日中国诸多经济、社会与治理难题及困境的关键之所在,也提醒我们耕地与土地政策对于国家安全与国家独立具有重大意义。这也说明未来中国的发展,无论是进一步的城市化的推进,还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推进,尤其是政府官僚系统的清廉与效能优化和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能力的加强,都亟需培育社会。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自由主义所标榜的“弱国家-强社会”从来不曾给哪个国家及人民带来福祉,更毋庸指望“弱国家-弱社会”,唯有“强国家-强社会”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国内秩序与国际安全及其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