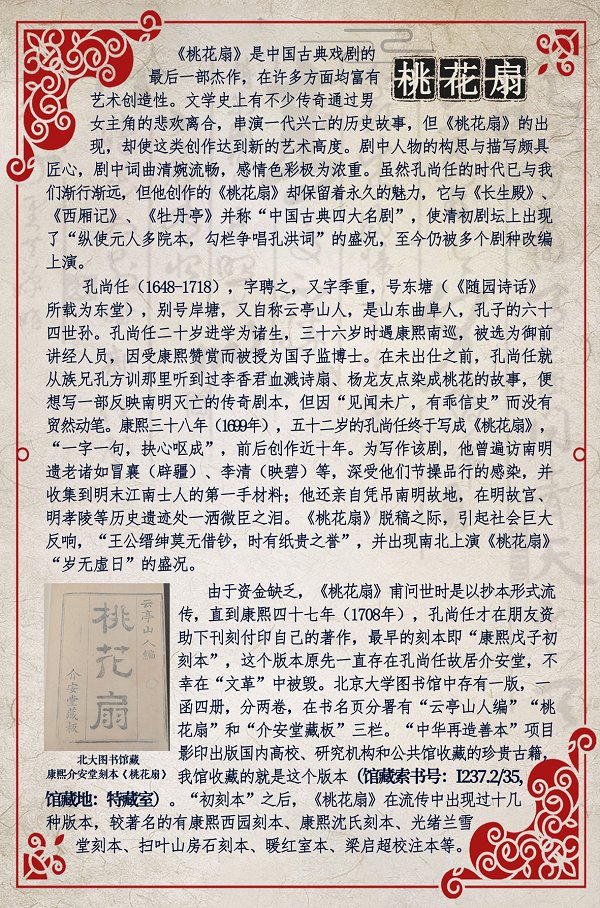


《桃花扇》是中国古典戏剧的最后一部杰作,在许多方面均富有艺术创造性。文学史上有不少传奇通过男女主角的悲欢离合,串演一代兴亡的历史故事,但《桃花扇》的出现,却使这类创作达到新的艺术高度。剧中人物的构思与描写颇具匠心,剧中词曲清婉流畅,感情色彩极为浓重。虽然孔尚任的时代已与我们渐行渐远,但他创作的《桃花扇》却保留着永久的魅力,它与《长生殿》《西厢记》《牡丹亭》并称“中国古典四大名剧”,使清初剧坛上出现了“纵使元人多院本,勾栏争唱孔洪词”的盛况,至今仍被多个剧种改编上演。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随园诗话》所载为东堂),别号岸塘,又自称云亭山人,是山东曲阜人,孔子的六十四世孙。孔尚任二十岁进学为诸生,三十六岁时遇康熙南巡,被选为御前讲经人员,因受康熙赞赏而被授为国子监博士。在未出仕之前,孔尚任就从族兄孔方训那里听到过李香君血溅诗扇、杨龙友点染成桃花的故事,便想写一部反映南明灭亡的传奇剧本,但因“见闻未广,有乖信史”而没有贸然动笔。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五十二岁的孔尚任终于写成《桃花扇》,“一字一句,抉心呕成”,前后创作近十年。为写作该剧,他曾遍访南明遗老诸如冒襄(辟疆)、李清(映碧)等,深受他们节操品行的感染,并收集到明末江南士人的第一手材料;他还亲自凭吊南明故地,在明故宫、明孝陵等历史遗迹处一洒微臣之泪。《桃花扇》脱稿之际,引起社会巨大反响,“王公缙绅莫无借钞,时有纸贵之誉”,并出现南北上演《桃花扇》“岁无虚日”的盛况。
由于资金缺乏,《桃花扇》甫问世时是以抄本形式流传,直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孔尚任才在朋友资助下刊刻付印自己的著作,最早的刻本即“康熙戊子初刻本”,这个版本原先一直存在孔尚任故居介安堂,不幸在“文革”中被毁。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存有一版,一函四册,分两卷,在书名页分署有“云亭山人编”“桃花扇”和“介安堂藏板”三栏。“中华再造善本”项目影印出版国内高校、研究机构和公共馆收藏的珍贵古籍,我馆收藏的就是这个版本(馆藏索书号:I237.2/35,馆藏地:特藏室)。“初刻本”之后,《桃花扇》在流传中出现过十几种版本,较著名的有康熙西园刻本、康熙沈氏刻本、光绪兰)堂刻本、扫叶山房石刻本、暖红室本、梁启超校注本等。
《桃花扇》是有着强烈真实感的历史剧,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说明剧中重大事件均属真实,只在一些细节上作了艺术加工。作者“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通过侯方域和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重现南明覆亡的历史。与主流的大团圆结局不同,《桃花扇》是少数能够将悲剧精神贯彻到底的作品之一。作者注意到历史覆灭之下人物悲剧性的命运,并通过人物的悲剧性结局更加清晰而残忍地向人们展示生活中存在的对立和分裂,而且作者也并未试图弥合这种分裂,去完成一个剧中人物寻找到出路的通常性结局。《桃花扇》的悲剧也是群体性的悲剧:一个朝代灭亡,造成的原因不是某一个人的过失,承担最后悲剧结局的也不是一个人,而面临悲剧命运进行抗争的也不只有一个人。在最后一出《余韵》,侯、李几经波折终于重逢,本打算夫妻下山还乡,却被作者借道士之口一语呵破:“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个人儿女情长无暇顾及,寻常百姓寥寥生计难保,君王颠沛流离半生凄惨,但最伤痛的是国之不国。《桃花扇》实写侯、李的悲欢离合,虚写家、国的兴衰荣败,虚实相生,韵味深长。
《桃花扇》在流传过程中也有多种改编作品出现,最早的是孔尚任的友人顾彩,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将之改编为《南桃花扇》,最大的变动是“令生旦当场团圆”,虽然孔尚任批评这个结局“仅以快观者之目”,但后来很多舞台演出使用了该剧本。
近代人改编《桃花扇》,一类如1937年欧阳予倩改编京剧《桃花扇》,1939年又改为桂剧,1946年再改话剧,这是在战争时期的背景下发挥《桃花扇》所蕴含的政治兴亡主题。另一类是发掘古典戏曲的风韵和重现历史沉思,如2008年上演的田沁鑫版昆剧《1699·桃花扇》,除原有的属于1699年的历史感和戏曲的旖旎,更多关注的是戏曲冲突中的人性美和历史遗存如古老昆曲的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