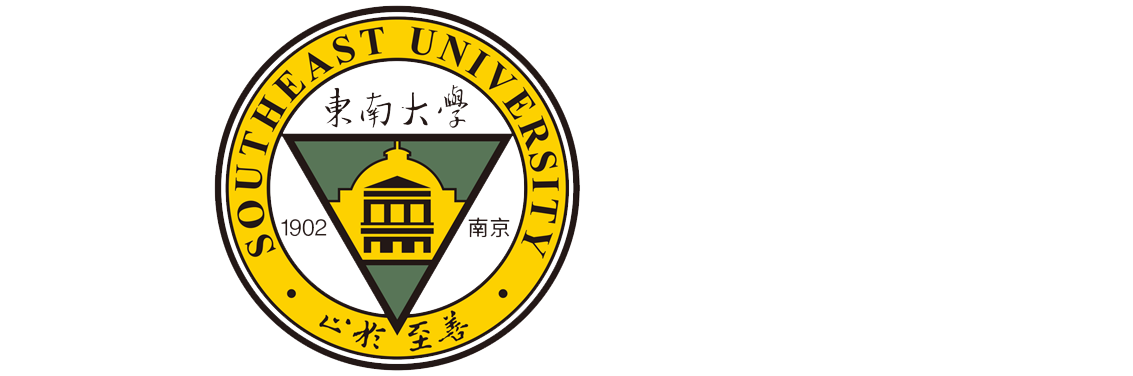老槐树在院角佝偻着身子, 枝丫摩挲着青瓦屋檐,似一位饱经岁月沧桑的老者,在时光的角落里默默诉说着往昔的故事。每年四月,洁白的槐花如雪花般簌簌飘落,轻盈地落进奶奶的粗瓷碗里, 她总是满含笑意地说,这是老天爷慷慨撒下的糖霜。
那时,年少的我常蹲在灶台边,专注地往炉膛里添着柴火, 跳跃的火光欢快地舞动着, 将奶奶佝偻的脊背映成一片暖金色的温柔。 她后颈的碎发不经意间沾着绒绒的槐花,宛如覆上了一层轻柔的雪,而木盆里浮着的细碎槐花瓣, 恰似揉碎了的银白月光,在水中悠悠晃动,泛起丝丝涟漪。
灶台上的铁锅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升腾起的雾气弥漫在空气中。 奶奶手持木勺,缓缓搅动着面糊,她手背上爬满的深褐色斑点,恰似老槐树皮上裂开的纹路,记录着岁月的痕迹。 她温柔地笑着,将冒尖的粗瓷碗轻轻推到我面前。 当我舀起一勺送入口中,槐花的清甜与麦香在舌尖瞬间散开,那美妙的滋味,如同春日里最温暖的阳光,流淌进心底。 我望着她那微微佝偻的背影,蓝布衫显得空荡荡的,仿佛一阵微风便能将她单薄的身躯吹倒,心中不禁涌起一阵酸涩。
我考上重点高中的那天, 奶奶满心欢喜,在院子里摆了三条长凳,又精心地把新鲜的槐花拌进糯米粉里, 蒸了满满两笼。“槐花要趁露水没干的时候采,” 她一边用竹筷戳着蒸好的槐花糕, 一边语重心长地说,“就像读书要趁早啊。 ”我凝视着她,只见她手背上沾着星星点点的面粉, 指甲缝里嵌着槐树汁的淡绿色, 仿佛藏着春天最隐秘的脉络。
高中住校后,每个周末回家,我总能在书包里惊喜地发现奶奶为我准备的晒干槐花瓣。 她把这些花瓣细心地缝进蓝布香囊,笑着告诉我,这小小的香囊能驱蚊。 直到某个暴雨夜,我提前回家,撞见她踮着脚,努力地够着树顶那盛开的槐花。 她枯瘦的手腕在风雨中微微摇晃,如同脆弱的竹枝,让人心疼。 我急忙冲过去紧紧抱住她, 那一刻, 我闻到她衣襟上经年不散的槐花香混着淡淡的汗味,那熟悉的味道,像晒透的棉被,裹着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人老了骨头脆,”她依旧面带微笑,往我手里塞着槐花,“你看这花多俊, 跟我囡囡一样。 ”后来我才知道,那年她不慎摔断了胳膊,却只是用艾草熏着伤处,强忍着疼痛,依旧在凌晨就去采那头茬的槐花。 那些夜晚,昏黄的白炽灯下,她守着我,一针一线地为我缝着新鞋垫, 针脚细密得如同精致的槐花纹路, 每一针每一线都寄托着浅浅思念。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 老槐树正簌簌地落着花。 奶奶站在树下,把纸张举在眼前,反复地端详着,阳光透过指尖,在她掌心投下晃动的光斑。“北京远着嘞。”她突然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像老槐树的年轮,刻满了岁月的痕迹,“槐花往北飞, 能飞多远呢? ”可就在执意要给我做槐花干粮时,她踩着板凳够树顶的花, 突然腿一软摔了下来,怀里的槐花撒了满地。 我心疼地哭着要送她去医院,她却紧紧攥着槐花不松手,念叨着:“死不了。 ”那天深夜,我听见她在隔壁屋压抑的呻吟, 月光把窗棂的影子投在她蜷缩的背上,像捆着无数根荆棘,刺痛着我的心。
第一次坐火车北上的清晨, 月台上的槐树在晨雾中轻轻摇曳,我趴在车窗上,看着她的身影渐渐缩成一个小点, 蓝布衫在风中飘成一片模糊的云, 泪水不禁模糊了我的双眼。
秋天总是来得格外早, 宿舍的暖气烘得人昏昏沉沉。 每到深夜,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奶奶的柴火灶, 那曾给予我无尽温暖的地方。 她来信说:“槐树今年开得旺,我给你蒸了槐花麦饭,放在灶台上。 ”信纸上沾着褐色的水渍, 像滴干涸的泪。 那天下午,我在图书馆翻到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读到“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时,忽然听见窗外的杨树叶沙沙作响,恍惚间,奶奶又在槐树下摇着蒲扇, 那熟悉的画面仿佛就在眼前。
大一下学期的深秋, 槐花再次开遍山时,我在图书馆接到了一个电话。 等我连夜赶回家时,老槐树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 院门挂着锁,锁孔里塞着干枯的槐花瓣。
我冲进空荡荡的屋子, 窗台上的槐花在月光下泛着灰, 旁边压着泛黄的信纸:“别难过,槐花明年还会开。 ”泪水不受控制地砸在纸上,晕开了墨迹。 墙角立着那根打槐花的竹竿,顶端还沾着去年的槐叶,像老人伸出的枯手,仿佛在诉说着曾经的故事。
出殡那天,雪下得紧,洁白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 送葬的队伍缓缓走过村口的老槐树,枝丫上还挂着去年的枯叶。 我忽然想起那个总沾着槐花的后颈, 想起她在油灯下补衣裳的剪影, 想起她最后说的槐花饼。 雪落在新培的坟土上,像撒了层没化开的糖霜, 仿佛是老天爷也在为奶奶的离去而悲伤。
如今每次经过槐树,我总会不由自主地驻足。 细碎的白花落在肩头时, 恍惚间, 我又看见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女孩,蹲在灶台边往炉膛里塞柴火,火光映得她的蓝布衫泛着温柔的光。老槐树依然在风中沙沙作响,仿佛在絮絮说着那些未曾说出口的话。
整理遗物时, 我在鞋柜最深处摸到个蓝布包裹。 抖开层层叠叠的旧报纸,露出半双未完工的鞋。 指尖触到某个凸起的针脚,那是奶奶留下的记号, 像土地在布料上凝结的霜。 针脚旁渗着暗红的血迹,在月光下泛着贝壳般的虹彩。 这一生也没有办法,有些告别要用余生来偿还, 有些远方永远在来的路上,而奶奶的爱,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如那悠悠的槐香,萦绕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