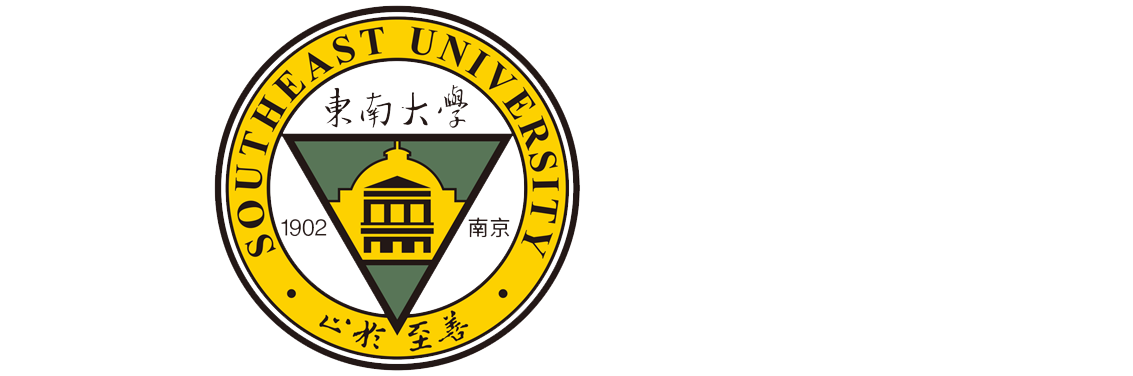熊庆来去世后,他的学生仍十分关心熊庆来夫人。1983年10月2日,严济慈(右一)、华罗庚(左一)前往中关村住所看望熊庆来夫人。
我和迪之结婚是旧式婚姻,我们十六岁就结婚了,当地有一个规矩,在新娘被引进洞房时,新娘要向新郎叩个头,叫“挑水头”,新娘叩了此头后,日后新郎才肯给新娘挑水,叩头之后,新郎还要跨一下新娘的头,这就不清楚有什么说法,总之还是男尊女卑的旧风俗。我当时按旧规矩向迪之叩了一个头,可是他不但没有跨我的头,反而还向我作了揖,亲戚和来宾看了,都赞扬说真有礼貌,我也很感动,心里暗暗生了敬佩之情。
一
我和迪之结婚不到一个月,他就到昆明去读书了,祖母问是不是你们感情不好,迪之说不是,只因读书要紧。
我和迪之结婚的第二年,那时还是清朝时期,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年轻人剪发以示反对清朝,他也受新思想的影响,约了些同学剪发,但外出时戴着有辫子的帽子。在国外留学时,他也专心学业,他写信回来给父亲说:“戏院酒店舞厅男不喜入,谚语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努力读书为要。”并且他认为跳舞就会和外国女朋友要好,就要和她们结婚,丢掉家里的妻子,这是很不道德的。1957年从国外回到祖国以后,虽年老病多(60余岁,又患高血压,半身不遂,糖尿病),他还兴致勃勃地开始学一门新的外国语———俄语。他认为研究科学必须多掌握几国文字。
二
迪之在东南大学任教时,创办了算学系,学生都很聪明用功,现在著名的科学家严济慈、赵忠尧、胡坤升都是那时候的学生,当时缺乏教材,他自己编讲义,他编了好多种讲义,我虽然不懂,可是那些名目都记得很清楚,叫微分方程、微积分、高等分析、三角、球面三角、偏微分方程,每种都是油印的一大本。他出的习题很多,学生做得又快,所以不但编讲义的任务大,出习题和改习题的任务也大,当时他又患有严重的痔瘘,在床上趴着工作,每天还要到学校去讲课。系里有个助教名孙唐,因为程度有限,不但不能帮着改习题,而且还做习题来让迪之改,他每天工作到深夜,我也陪着他坐着,替孩子们做鞋织毛衣。我在青年会学会了打毛线、做鸡蛋糕,还学了一点英语。
迪之埋头工作从不为家务分心,我也不让他为此操心,当他第一次出国留学时,我在封建大家庭中要做很繁重的家务,做很多人的饭菜还要喂猪,但家庭不给零用钱,连做衣服的钱都不给,我只好在把大家庭的事做完后,晚上替人家剥花生米,用砖头碾破花生壳可剥得很快,每晚可以剥一斗,换来的钱买布做衣服给孩子和我自己穿,衣服也是我自己做。孩子发高烧生病没钱请医生买药治病,当地有个土办法:捉五个蟑螂(有翅、黄色的那种蟑螂,不要无翅花色的),去掉头、翅、腿、内脏,只要胸部的肉,再放三片生姜在一起煮水给孩子喝,出一身汗,第二天就退烧了,病就好了,倒很有效。
三
我的祖父是举人(姜小峰),父亲(姜元英)是廪生,可算书香之家,但是对女儿的教育并不关心,大概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我未结婚之前,认得的字很少,连我姓的“姜”字都不认得。结婚后,迪之认真地教我认字、写字,后来会看小说,能自己给迪之写信。不过学习的时间不多,又很短。婆家是个大家庭,有太婆、公婆、伯父婆、有丈夫的兄、弟、妹、侄子、侄女一家二十多人。
大家庭的家务很重,迪之在法国留学,我偷空写信,一封信要写好几天,不会写的字得问人,也是很困难的。迪之去法国的第二年,公公便娶了一个品质恶劣的妾,婆婆忠厚软弱,小辈媳妇不但辛苦不堪,还要挨骂受气。迪之离家八年,他回家先接我到昆明,几个月后去南京,算过了三年幸福的日子,不过这三年也不是无忧无虑的。
当他在东南大学任教时,曾患肋膜炎住院,因为医院条件差,所以我每天把做好的饭菜送给他吃,我自己吃医院的菜饭,早上送牛奶面包给他,我吃医院的稀饭、咸菜,然后我回家买菜做饭喂孩子吃奶,中午又做了合口的菜饭送到医院给他,我又吃医院的饭,晚上也是如此。在他病未出危险期时,需要我陪他住在医院里,当时夏天蚊子很多,医院没有蚊帐,我就把家里的蚊帐给他用,自己只好让蚊子叮。
迪之第二次出国深造,家里一切事务都由我一人承担起来,那时大儿子在清华大学念书,二儿子他带到法国,另外三个小的孩子由我带到南京去住,这两年迪之在法国得了国家博士学位,代价很不小,他有教授的薪水,在当时是很高的,在法国的第一年可以享受休假的半薪待遇,但是第二年就没有了,他在国外带着一个孩子,花费不小。
我住到南京,因为在南京我们有点平房,可以收房租金50多元,补贴生活,我每月寄30元到北京供给大儿子和他的五弟 (在崇实中学念书)上学。我依靠剩余的20多元带着三个孩子生活,我们生活非常节省,顶多买点牛肉给孩子吃,我在门前种点瓜豆、蔬菜。三个孩子曾轮流生病,七岁的女儿患白喉发烧到40℃,去了几个医院,都不肯收了,只好我自己医,正好有一亲戚告诉我说:“你给她擦薄荷锭在喉咙上,每天擦三次就可治好。”我就用这方法,果然把孩子的病治好了。
我们另外两个孪生孩子同时上吐下泻,我昼夜守护着他们,熬得精疲力竭,其中一个孩子由上吐下泻转为伤寒病,诊断迟了,最后请一名医夜里来出诊,次出诊费是14元“大头”,这医生说孩子病入膏肓无法医治了。这孩子很聪明,我买了些看图识字挂在墙上,教他的孪生弟弟学,因他病未好没有教他,但弟弟还不会,他在旁边已学会了,不幸夭折时他才四岁。我不敢写信告诉迪之,他正在巴黎,我怕这消息影响他工作的情绪。好多次家里发生事故,迪之都恰好不在,一切困难都要我一个人想法克服。
四
在清华大学任教时,迪之工作起来废寝忘食,每天中午我都得打三、四次电话催他回家吃饭。在云大任校长时,校务已经繁忙,他还每周担任几小时的数学课,这完全是尽义务,没有额外报酬。因为他觉得学生的数学程度低,他要尽可能提高他们的学习质量。
他第三次到法国,住了八年。生活艰苦,又患半身不遂,就在这情况下他继续做数学研究工作,有不少成绩。我在国内,因迪之的父亲在家给些田地,我被认为是地主,押回老家关在间黑屋子里,很经受了些苦难和惊骇。1957年他回到祖国的怀抱,看到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万分兴奋,作了不少的诗和文章来歌颂新中国。当他从收音机里听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时,我坐在他旁边见到他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高兴地说:“我国也有原子弹了!”
迪之虽半身不遂,仍孜孜不倦地用左手写论文,刻苦钻研数学、辛勤培养学生。在他已是七十高龄的时候,还接收了两名研究生———杨乐和张广厚。这是他一生中最后培养的两名学生。因他年老有病,领导照顾他在家里工作。每天吃过早饭他就伏在桌上工作,下午晚上也是如此,自觉地、积极地工作。在文革中,虽受了不少折磨,但他始终没有怨言,总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直到临终前这天在他写的一个检查中,他还表示要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们夫妇生活几十年,一直相敬如宾,和睦相处。迪之离开人世已十一年了,但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注:熊庆来 字迪之
本文来源于《熊庆来传》第二版(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文章写于1980年)。
(张安桥、汤咏芊和肖珺心三位同学根据该书电子版录入)